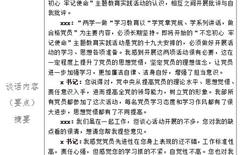浅析梁晓声后期作品的创作风格
发布时间:2014-08-16 11:53:32
发布时间:2014-08-16 11:53:32
1 引言
作为知青作家代表的梁晓声,以《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进入文坛后,笔耕不断,创作出了为数不少的优秀作品。梁晓声的前期作品主要是知青小说,知青文学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在现当代文坛上占有重要位置,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它更多的来自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刺激,有着自己的精神资源,有着对时代的独特体验和思考,有着对时代或含蓄或直接的反应”[1]而梁晓声在知青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与其他作家相比,他的知青小说着重于表现在困惑中的思索、奋进坚持和对自身经历的肯定,充满了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激情,因此评论界常以“青春无悔”来定义他的知青作品。梁晓声在知青文学中的代表作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今夜有暴风雪》、《荒原作证》等,塑造了李晓燕、曹铁强、裴晓云等一系列在那段荒诞岁月里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形象,他们把的全部信仰付诸到了这片土地,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至善至纯的真诚,坚毅和无限的牺牲精神。梁晓声先期创作笔调粗犷雄浑,思想豪壮奋进,充满理想主义的悲壮美。
进入九十年代,梁晓声把创作焦点对准社会底层人民,将强烈的道德观念注入其中,冷眼旁观,这世间人情冷暖。他为民立言,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表达他对社会现实敏锐的洞察和感悟,向我们展示着平民阶层的生存图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出了《父亲》、《司马敦》、《学者之死》、《贵人》、《浮城》等优秀作品。通过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酸甜苦辣,聚散离合,他们也有追求有执着,但却与现实充斥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他们的理想幻灭时,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其中的无奈、愤怒和反抗。
在评论界一致受到高度肯定的是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他所表达出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鼓舞了一代青年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为阴沉的文化氛围增添了一种激情和积极向上的力量。王蒙曾对梁晓声作过这样的评价:为知青树了一块丰碑。对于他90年代后的创作,关注度相对减弱,而且褒贬不一。
2 晚期风格形成溯源
作家的创作倾向和风格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与社会发展,社会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一个作家创作道路都能显示出时代文化的痕迹。当中国走上现代化建设之路的时候,世俗文学日益兴起,对于梁晓声而言,时代的变化和自身经历的变化,引导他从“知青情结”中走出来,将目光投向了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生活。这是一个社会转型和个体经验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必然文学现象。
2.1 底层叙事的个人原因
底层是孕育苦难的天然场所,梁晓声面对底层生活,并不是居高临下的俯视,而是把人文精神融入其中,同样以平民的身份对晦涩的生活境遇发出质疑,揭示底层人民的人性之光。从佛洛伊德的观点看,一个人成年后的思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过去的经历,那梁晓声平民意识的形成也来源于“过去的经历”,事实确实如此:梁晓声经历过贫穷,生存扎根于底层人民之中,他熟悉平民的生活,希望通过手中的笔去书写他们;另一个方面,从贫穷中走出来的人更深刻的知道贫穷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继而会转变成一种同情,梁晓声正是怀着这种同情,抛开文学对社会批判性、触动性、改造性而去关注底层人民的。这使他的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
梁晓声的很多作品都写到了自己的童年经历,从梁晓声自述中我们可以知道:梁晓声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建筑工人的家中,其“祖上尽是文盲”,父亲在外工作,一家人挤在一个小破屋中,他家经常受到其他人的欺负,在那个小院中过着“下下人”的生活。因为家庭的贫困,梁晓声在班里被人排挤鄙视,小小的他就体会到了贫穷带给人的畏惧,他因此而自卑,甚至不想去上学。晚上的时候,母亲经常给他讲一些民间传说和戏曲故事,秦香莲、王宝钏、杜十娘、包公传等。这些故事曲折生动,蕴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而且贴近平民生活,坚守平民立场,传达平民情感,既能起到教育引导的作用,也使梁晓声在这种感情倾向的渲染下,习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去感知生活。
贫穷带来苦难,梁晓声出生在社会最底层的家庭中,这些贫穷的经历伴随着梁晓声的成长,让他对苦难生活的描写始终难以释怀。他对贫穷的敏感,对苦难的情结,使他赋予了出身底层的人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以至于他的大多作品主人公都是来自贫困家庭。《苦恋》中那些生在农村的女孩子们,同样对爱情有着纯洁憧憬和坚守,却被封建思想和残酷的现实所残害。《贵人》中的芸和素,两个出身贫寒却不甘平庸的女大学生,为了得到追求前程的经济基础,不惜牺牲自己的爱情与身体,委身于各自的“贵人”,我们鄙视唾弃她们的同时,又怎能不去同情怜惜她们的命运呢。还有《荒弃的家园》里的芊子,《表弟》中的表弟等等,这些小人物,他们生活在最不起眼的地方,过着不起眼的生活,可也正是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最为真实的一面。梁晓声在这些作品、这些人物中倾注了无限的真诚。
1968年,梁晓声插队北大荒,开始了知青生活,先后当过农工、小学教师和报导员。在这一时期,他满怀“红色”热情,投身到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和所有的知青们共患难,直到最后走上文学之路。经历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上一辈革命者,大都存在“知青情结”,梁晓声同样也是,正是因为珍视这段回忆,将浓挚的感情投注到其中,才成就了梁晓声在知青文学中的辉煌。其实,知青群体是平民阶层的一类特殊人群,它是顺应特殊时代而产生的,它加深了梁晓声的平民记忆,让他再也无法远离平民阶层。之后离开北大荒到北京城,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梁晓声也从“知青情结“中慢慢淡化出来,创作的视野随之而变。面对退却了英雄主义光环的庸常的人们,他依然将写作的镜头对准了社会最底层的人民。
梁晓声的出身,他的生活经历,都已经注定了他与平民阶层的不可剥离。那些苦难的岁月对于他来说已经渐行渐远,他已经“无法还原于苦难的历史处境,反观过去,苦难仅仅成了此时庆幸有余的代价。”[2]时间会把苦难过滤,留下来的,将会是特殊的美感。对于梁晓声而言,这些苦难是他宝贵的生命经验,也是使得他在当代作家群中关切平民生活尤为突出的根源。
2.2 底层叙事的社会原因
作家都是时代的产儿,梁晓声也不例外,他所处于的时代决定了他的生活命运,同时也决定了他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80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促进了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受到了外国文化的影响。社会的转型打碎了一部分人对改革不切实际的想法,也给思想文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首先,经济多元化为思想多元化提供了社会条件和氛围,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又促使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这些都要求人们用相应的话语去重新审视和评定这个新型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逆反,使人们不再执着于单纯的信仰,而开始注重利益的获取和自我享受。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被腐蚀消磨,物欲的赤裸裸的膨胀,使道德、理想、责任不断淡化,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财富的过分集中和贫富差距不断增大。九十年代以来,对于“人文精神”的变质,不断的遭到思想文化界的质疑。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引发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在当时的文化情境中实现与商业文化、经济意识形态的对抗,这在当时仍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梁晓声平民创作提供了思想基础,这正如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对于伤痕文学的影响一样。
随着经济的高速运转,致使中国社会阶层开始分化重组,梁晓声在《中国社会主义各阶层分析》中写到:“对中国而言,生产力正在摆脱落后,经济基础正在摆脱虚弱,商业时代正方兴未艾地孕育着,阶级正日益加快地分划为阶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新的平民阶层也开始重新聚合。他们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拥有自己特有的经济收入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特别是他们形成了自己的阶级意识,成为当代社会上新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生活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对他们的关注也是文学所不能忽视的。因此在这个时期,一批优秀的作家超越改革文学的局限,开始对我国整个历史进程进行反思。其中有:张承志、韩少功、梁晓声、刘醒龙、谈歌、张炜等。这些作家的现实批判是历史与道德的完美统一。他们的批判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二是追求大写的“人”,倡导惩恶扬善。
梁晓声因此也意识到创作中张扬的“人民性”应该是默默承受历史后果的平民大众,而非历史开拓成果的享有者。而此时,不断壮大的平民阶层作为读者也要求文学可以现实化,那些距离他们生活相对较远的文学作品则被他们所摒弃,他们希望文学可以表现平民生活,可以表达他们的思想和追求,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对于平民文学的需求急剧扩大,与此同时文学家们也开始调整自己介入社会的角度。因此,梁晓声平民化的创作风格是文学和平民阶层双向选择的结果。
3 晚期创作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仔细的品读梁晓声的后期作品,就会发现有一条起伏的感情线贯穿其中。无论从叙事内容,叙述手法还是人物形象的刻画,都是在慢慢发展变化的,不变的是其平民的叙事角度和立场。梁晓声寄予在作品中的感情经过了由脉脉温情到迷茫颓败转而犀利的过程,这是社会现实不断转变在他眼中的映射,他对平民阶层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但同时也对这个社会越来越深的道德堕落、人性丧失发出了质疑和批判。我们从梁晓声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集《弧上的舞者》中,可以理解到梁晓声用“弧”的意义来定位自己,始终围绕着平民阶层这一核心,进行自己的创作,而且为了更准确更贴切地表达平民世界,他也在不断地摸索寻找到底应该“站在社会之环的哪一段弧上呢”,梁晓声始终就像是一个和读者面对着面,蹲着谈心的人,离我们很近,他一直默默地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命运,在平民化创作的道路上不断追寻。
3.1 梁晓声的温情叙述
历史对文革的否定,对于那些充满理想主义、“红色”热情的红卫兵青年们,无疑是一种情感上的伤害,曾经以为的当家作主、轰轰烈烈,为此付出的青春和汗水,在十年之后被证明只是政治上的工具。他们的苦苦追求变得不再有现实价值,就像是被无情出卖的英雄,用自己的豪言壮志换来了历史的抛弃,这给他们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失落感。梁晓声也发出过“仅仅用同情的眼光将付出了青春和热情乃至生命的整整一代人视为可悲的一代人,这是最大的可悲,也是极不公正的”这样的感慨。
所以,当他把目光渐渐从知青身上转移开,在后期创作的最初阶段里,梁晓声更关注于平民生活中温情感人的生活场景。当激情成就了历史不经意的荒谬和错误,当失落迷茫开始占据心房的时候,梁晓声更愿意把受到挫折的心交还给他最依赖的平民阶层。在最初的时候,梁晓声将诗意化、浪漫化的手法融入到对平民生活的叙述,创作了《父亲》、《母亲》、《黑纽扣》、《人间烟火》等一系列亲情小说,主要是挖掘平民生活中的种种不平凡,赞美他们纯真的亲情爱情,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着力表现平民在逆境中不屈的抗争精神,迷茫中的坚毅勇敢,让人感受到平民在灰暗生活环境下的温情之光。对生活中情感的描写,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它是感动读者,使读者产生共鸣的桥梁,罗曼罗兰就说过这样的话:“在客观的写实主义上还必须加上使它温暖的心灵的抒情主义”,[3]梁晓声正是做到了这一点。
在梁晓声转型之后最初所创作的亲情小说中,融入了大部分自己的亲身经历,把小说的虚构性降到了最低,他所刻画出的“父亲”“母亲”的形象代表了曾经那个时代的父母们,他们生在旧社会,经历了那个年代的苦难波折,政治纷争甚至是战争:“六岁给地主放牛,十二岁闯关东,亲眼见到过国民党怎样残害老百姓,也被日本人抓过当劳工,要不是押劳工的火车被抗联伏击,很难想象,他今天还活着……”就是这样的老一辈父母亲们,他们没有很高的文化知识水平,也不会用柔声细语表达内心的感情,他们只是会严厉的批评或者无言的沉默,但是他们的爱却是无比的深沉和凝重!梁晓声说过:“母亲不仅把她要强、硬朗的性格传给我,还把她做人就要做一个有同情心的,孝道的,善良的,正直、正派的人的思想传给了我”。他创作的这些亲情小说正是对曾经忧伤而温馨的过往的追忆,这些文字读起来哀而不伤,悲而不苦,洋溢着积极向上的精神品格和浪漫情怀,把脉脉温情注入读者心间。
3.2 梁晓声的犀利转变
随着阅历的增长,梁晓声越来越意识到平民阶层在社会变革下的惶惑无措、痛苦挣扎,发现那种单纯乐观,理想化人物的空泛性。于是,浪漫诗意的叙述在他作品中日渐衰颓,笔锋转向犀利、激愤。他不再只是描写平民中的欢声笑语,更将平民在社会变革之下的困境,面临的社会问题,还有生活的阴暗面展示给我们。这一类小说包括《又是中秋》、《学者之死》、《荒弃的家园》、《贵人》、《表弟》等。
《又是中秋》是其中的典型作品,它为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随着世事的变迁,在商品化经济大浪潮的冲刷下,迷失自己的故事。老隋是曾经的辉煌和最后的结局——因诈骗被捕,构成了警为人世的对比,《又是中秋》“通过老隋这样坚定的文学分子的堕落和颓败,写出一个时代是如何被金钱至上主义所俘获的……其中所包含的深刻意义,洞穿了这个时代的政治与资本构成的宏大的历史异化感。”[4]是这一时期很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让我们对市场经济发展这一把双刃剑,有更深刻的体会与反思。
此时期另一震撼人心的作品就是《荒弃的家园》,怎么都不愿相信芊子这个善良的女孩为了奔向城市新生活,居然亲手烧死了自己的母亲。芊子的残忍和堕落,是令人心痛和惋惜的,故事的结局也残酷得让人不忍去看,掩卷沉思,故事的悲剧性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芊子被城市生活所吸引,义无反顾的想要叛离自己的故土,这也是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被追求更高层次物质生活的思想所牵引,一步步走向弑杀亲母的自我毁灭。人生不应该是如此残忍的追求方式所收获的,我们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城乡差距,而这些不是用杀害亲人,背弃故土来实现的。梁晓声,这个始终和我们平民大众站在一起的作家,他是怎样痛心的看着这些迷失者的自我毁灭,来写下这些文字的。他用自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赤诚的忧国忧民情,为我们展示时代前进中的缺陷,对人性道德的丧失发出了强烈的批判。
3.3 梁晓声的魔幻写作
90年代中后期,金钱至上和道德缺失的价值倾向似乎已经覆盖大局,对于底层人民在改革过程中的困境、迷失甚至是自我堕落,梁晓声慢慢感觉到在作品中用传统道德来呼吁和反抗,已经显得有些无力。一个人,无法力挽狂澜,在人们越来越醉生梦死,自我麻痹的环境中,那些泛滥的人性丧失,和物质所带来的欢愉,使很多人彻底地迷失自己。于是,梁晓声进行了最激愤的一次反抗,写作转向了盲从与魔幻,一系列荒诞性的作品由此产生:《浮城》、《大鸟》、《红晕》、《尾巴》等。在这些作品中,作家用悬疑甚至恐怖得手法营造了一个个背叛、血腥、杀戮的恐怖场景,让人不忍去读不忍去看。这个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相互怀疑,为了保全自己而去疯狂地伤害别人,他挖掘到了民族深处的劣根性:嫉妒、猜疑、游戏人生,将人性丑恶的一面毫无遮拦的摊在我们面前。梁晓声始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用这些残酷的文字为我们敲醒警钟,他把自己的创作融入到历史文化的对照和思考之中。
《浮城》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和评论者的关注,《浮城》不同于梁晓声的往日作品,它使用超现实的魔幻手法,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充满杀戮、罪恶、残暴、扭曲的虚幻的城市,是一篇荒诞主义的警世之作。《浮城》的诞生标志了梁晓声对社会物化腐蚀的近乎执拗的新一轮批判。作品中的浮城显然是一个虚幻的城市,这里充满了混乱和扭曲:大难临头时人性恶的疯狂,梦幻破灭时游戏般的残忍,同胞互憎的丑恶等等,一个接一个丑陋的场景在我们眼前上演。梁晓声在这里为我们揭示了“我们熟悉的民族心理病根,比如:中国人的自私自利、中国人的缺乏严格意义上的信仰、中国人的恃强凌弱……梁晓声通过《浮城》让人明白,浮城上人们的真正悲剧并不在于城市和大陆断裂了,而在于人们心灵处于无理性状态。”[5]
古人云:“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讲的就是物极必反。我们可以体会到梁晓声对社会道德沦丧的焦急和力挽,但是,他的这些作品把现实世界魔化了,他说:“我常郑重地标榜我坚持现实主义,可连我也不得不开始将现实主义荒诞化、魔幻化,‘逼上梁山’ 常使我倍觉内心不是滋味”[6]此时的梁晓声激愤掩盖了理智,过于偏激和片面,他是把人性丑恶的一面统统挖掘出来拼凑到了一起,就像是快感的宣泄,也令读者对作品中描写的丑恶画面产生了反感。
4 文本艺术性的独特体现
梁晓声的底层创作具有独特的艺术性,他以创作为生活而不为艺术的创作理念,用其带有泥土味的文字语言,为时代描述了一个完整的平民世界,表现了底层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温情、苦难、挣扎和迷失。他的作品就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从镜子中,我们可以找到某个人,原来就是我们自己。当创作风格逐渐确定的时候,就是一个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反映在语言文体方面,梁晓声原生态的叙事语言,平民形象的人物刻画,独特的悲剧色彩都是其平民创作风格的独特体现。
4.1叙事语言
“文学的根本材料,是语言——是给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思想等以形态的语言,文学是借语言来作雕型描写的艺术”,[7]梁晓声的文字独具特色,他用平民的语言来描述平民的生活,形成了独特的“梁式风格”,熟悉他的读者,只透过一段话或一个句子,就能识别出文字背后的他。相比于文学中华丽打磨的文字,梁晓声的语言更具平实和生活化,我们可以嗅到其中散发的泥土味和烟火味,也可以说,他的文字是粗粝锋芒的原生态语言,缺少修饰打磨却亲近生活,这也正是他为生活而写作的创作理念的体现。梁晓声对于文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取舍是十分理性和清醒的,有些时候,他宁愿为了思想而舍弃作品的艺术性,他选择了为平民而写,并不是为评论家而写,这正是他的真诚和执拗之处,也恰恰是如此,才吸引了相当一批读者舍弃那些轻巧流丽之作,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梁晓声。
梁晓声的语言是扎根于我们生活所在的厚实的土地之中的,在其后期创作的初始阶段里,梁晓声的文字充满的是温柔平实的感情,就像是一泓温泉默默流淌。在《母亲》的开头,梁晓声是这样写的:
淫雨在户外哭泣,瘦叶在窗前瑟缩。这一个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我觉得那是一种凝视。
我多想像一个山东汉子,当面叫母亲一声“娘”。
“娘,你作啥不吃饭?”
“娘,你咋的又不舒坦?”
这样的文字,读着让人感动,尤其是“娘,作啥不吃饭?”“娘,你咋的又不舒坦”,这两句山东大汉的问语,带着土土的山东汉子的味道,深刻地表达出对母亲的想念和爱,文字中渗透的人情味,正是梁晓声追求温情阶段的体现。而在《荒弃的家园》中,我们又体会到了文笔犀利的梁晓声:
芊子一点儿也没心软。她用一根手指往娘的额头正中间一戳,解气地说:“就你,还有资格跟我闹脾气?以后,只有我不高兴了骂你,你老老实实听着的份儿!就是我不高兴了打你,把碗往你脸上抛,你也要一声不吭地挨着,明白不?”
这是翟村在只剩下芊子和老弱病残之后,芊子对待母亲的一个场景,这些话读着让人冷到了心里去,长期的压抑导致了芊子心理的扭曲变态,直到最后她将自己的母亲烧死。这其中,充满了梁晓声对平民生活中的困境的无奈,同时也透露出一种对现实不满的酣畅淋漓的快感。这些文字同样在追求原生态,梁晓声在创作它的时候,一定很用心的在运用语言,包括每一个标点符号在内。
梁晓声九十年代后作品的语言显得俗白浅易,如此原生态的语言风格展现了社会的最真实的状态,它最接近也最能体现生活,它拉近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让读者在阅读时有一种亲近之感,使原本粗粝锋芒的语言变得有魔力般地被平民大众所接受并欣赏。
4.2 人物形象
梁晓声90年代后的作品为我们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底层人物形象,这些人物附带的故事无论是善良的、邪恶的还是挣扎的,都摆脱不了在理想和现实夹击下的所表现出的欲望。人是因欲望而存在的,对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的追求终是人心底最原始的欲望追求。梁晓声对于底层人民在历史潮流下的生存状态有着特别的关注,他表达平民心声,诉说平民情怀,同时也是对人性欲望的书写。底层形象的塑造是平民化创作风格的集中体现,所以必须切入到人性深处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的表现平民世界,梁晓声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商品化大浪潮下彷徨的知识分子,在城乡交叉地带挣扎的大学生,是怎样面对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生存真实的。经济上的匮乏,注定了他们要在这花花世界中苦苦追寻,无法逃离命运的掌控。
《沉默权》中的人物是梁晓声笔下农民形象的典型代表,写出了农民在居高临下的权势欺凌下的惶恐无措以及历史上逆来顺受的奴性。在基层邪恶势力的魔爪之下,郑晌午最后选择了用死亡来对抗现实的不公,这是最悲哀也最悲壮的解决方式,郑晌午用自己卑微的生命向残酷的现实发出悲愤地声讨:“我死给他们看,也死给社会看!”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底层的苦难,更看到了底层人民所蕴含的无比坚韧的力量,这种力量包含了多少辛酸和无奈。这些小人物在想得而不能得的欲望中挣扎反抗,由此引发的悲剧正是文本主题的意蕴所在。
《泯灭》写出了一代知识分子被金钱腐蚀,迷失本性的过程。主人公翟子卿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作家,在这样强烈的欲望支撑下,翟子卿就像是一个不倒翁,无论面对怎样残酷怎样不平的境遇,他都可以坚强去面对。但是,在他饱尝了“作家围城”里的痛苦后,他的作家理想,像梦一样消散了,他的价值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仿佛大彻大悟了一样:“金钱可以用来建筑豪华壮丽的大厦而不易倒塌,使人联想到‘永恒’这个词。而作家完成作品后,还得四处找门路请求出书,而且不能流传……在金钱面前文学不过是印钞机的机器甩下来的边角纸。”从当作家的理想转为对金钱的追求,这种欲望的转变,将翟子卿的人生转向歧途,他看透现实,执迷于金钱让他丧失本性无法自拔,那些镌刻在年轮上的苦难与亲情,也唤不醒灵魂泯灭的翟子卿。
在梁晓声塑造的形象中别有风情的一类就是女性形象,在《梁晓声自述中》系统地写出了作家对于50年代到90年代女性形象转变的一些看法,这些转变主要围绕着女性对于“性爱”的态度转变而变换.是对世纪末女性形象的进一步阐释。
《浮城》中塑造的婉儿是近现代小说人物画廊中罕见而独特的艺术形象,她的身上集合了复杂的性格特征,美丽与淫邪同存,卑污与动人相交。婉儿出身贫穷,年幼丧父,理应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女孩,但是她却以自己的青春和姿色为资本过着寻欢作乐的生活。她用“玩爱”的方式放纵自己,同时也被男人玩弄、勾引。婉儿 “淫荡如同艳鬼”但同时又“单纯得仿佛青春少女”,“她对二铁的怜悯,对孙寡妇的同情,对孙奶奶的挂念,对老孟祥感恩的心情。这一切都让我们深深地感到,欲望的放纵并没有彻底地吞没婉儿”[8]当她被赵晓坤所救并经历生死考验后,她对赵晓坤产生了感情。这份感情,拯救了思想沉沦的婉儿,她决定要做一个“漂亮的,可爱的,温柔的,活泼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语都证明自己是很有教养的“女人,纯爱情唤醒了婉儿纯真的心,在浮城里的那个乱世中散发奇异的色彩。婉儿是90年代都市女性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思想开放的典型代表,混合了妩媚与纯情,虚伪与善良,放荡诱与虔诚,她极具魅力和毒性,但都没有完全淹没她善良的本性。婉儿最终还是死了,这是隐藏在她复杂性格背后的必然宿命,也是浮城之中人们注定的结果。
穿插于女性背后的线索就是女性之于“性”的认识与解读,“性观念是一个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经过长期的道德熏染而逐渐形成的对于两性关系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人类经过漫长的文明进化,才把原始的单纯的动物性的性欲发展成充满精神内容的性爱活动。但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又常常存在着性与爱相分离,即无爱之性或反之无性之爱的问题”[9]《浮城》中的婉儿正是随着社会性观念的开放而不断放纵自己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使中国女性的思想相对保守,三从四德禁锢着女性的身体和心理,在商品化大浪潮的冲击下,“性”的解放随之而来,相较于曾经神圣的“性”,现社会的性是泛滥而缺乏精神内涵的。在某些情况下,“性”可以成为交易的手段,是女人对于男人致命的砝码,就像《贵人》中的芸和素。
大学生一直都被认为是“时代的骄子”,芸和素正是这样优秀的大学生,最后,却在理想与现实失衡的挣扎中,走上了不归路,他们出卖了爱情和身体,委身于“贵人”只为筹取考研所用的资金,我们似乎很难对她们的选择简单地致于肯定或否定,她们只是单纯地想要寻求更高的学历和知识,获取理想的工作,但是出身贫寒的她们在无奈之中选择了这样一条让人寒心的道路,我们到底是该责怪她们的幼稚,还是去向社会寻求答案?天赋人权,人应该是生而公平的,可是我们该向谁去索要这份公平。梁晓声通过对婉儿、芸、素等世纪末女性形象的描述,对物化时代中人性沉沦进行了发人深思的批判。
4.3 悲剧精神
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0]梁晓声的创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但这决不影响到其悲剧意识的表达力。因为“底层文学产生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产生于中国社会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因其表现了这一进程中底层民众所承受的历史性悲剧命运而具有深刻的悲剧精神。”[11]悲剧精神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怀,尤其是现阶段的中国还无法摆脱“现代化的阵痛”,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底层人们的困厄和挣扎,所以现实关怀在此时显得很是重要,曹文轩认为:“悲剧精神的觉醒,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觉醒,也是中国历史的觉醒。”[12]梁晓声九十年代的创作正是植根于改革开放的现实土壤中,展现时代转型中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对他们所承受的时代创伤给予道德关注和文化体恤,这本身就具有时代悲剧的精神。
梁晓声的底层叙事让我们看到了城市文明掩盖之下平民阶层隐秘的苦难,他用独特的视角展示了特定时代的平民大众的生活图景,从而具有平民悲剧的色彩。当苦难成为悲剧内容的时候,是对苦难的净化和崇高——唤醒时代沉沦的精神和个人良知的颓丧。如《沉默权》中农民郑晌午夫妻自戕的悲剧,《表弟》中肖冰死于精神崩溃的悲剧,《喋血》中平民大众之喋血被滚滚历史潮流所淹没的悲剧,都深刻地揭示了时代前行中人性的堕落,小说的深刻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对人物精神内心的揭示,更主要的在于对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的挖掘与呈现,它触摸到了平民阶层历史性的命运悲剧。
纵观同时期平民作家,在悲剧性这一方面,池莉侧重于表现人在现实面前的无奈感:“理想还没有形成就被现实所取代”。[13]方方则更多的是通过展示人物生存状态来表现的,是一种人物自身的性格悲剧。相较而言,梁晓声则更深刻清醒地去挖掘个体悲剧的复杂社会根源,将平民阶层的悲剧提升到历史社会的高度进行严肃地审视。所以,梁晓声寄寓在悲剧人物身上的,并不是一般人生之中的悲欢离合,而是个体存在和现实社会冲突下产生的社会悲剧,其悲剧性更显深刻和凝重。
5 后期创作的局限
梁晓声在当代作家中算是一个相当高产的作家,而在当今的文坛地位却不是很高。他的文学其实没有多少“纯文学”的诉求,只是充满了很多和现实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细微的东西。梁晓声的创作,几乎没有技巧策略的变化,他从来都是以纯朴的写实风格和粗粝的修辞策略来进行写作的。梁晓声的知青小说在文坛创下了辉煌的一篇,但是客观的说,身为作家的梁晓声经历了因苦难而辉煌,然后荣极而衰的过程。
梁晓声的作品中流露了悲天悯人和现实的无可奈何感,而充满理想主义的他,同时又想超越现实,很热情地去表达他的理想道德情操,挖掘人心深处的美好。当这些混合在一起时,则是理想主义者面对现实的一种痛苦。这使他的创作独具特色,同时也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泛滥的道德化倾向淡化了历史意识,过多的人生说教忽视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过于外露的主观宣泄使文本缺少含蓄,塑造人物时注入了太多的必然性与逻辑性,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物的个性。
他后期的一系列富于梁晓声特色的“自白体裁”作品,以大胆强烈的泛道德化激愤,直指社会现实,而太过的道德注重让他忽视了很多东西,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深度的匾乏。有论者认为梁晓声“暴动易怒、嫉恶如仇,拿道德激情抵抗社会转型期市场化过程中的商品经济,同时也把正剧演成了闹剧,很容易让人看到其无力的一面,甚至时感矫情或者作秀。”[14]这种浮躁的道德激情的膨胀,在其后期创作中越来越明显,特别是长篇小说完全屈从于商业时代写作的特征,如《浮城》、《泯灭》、等,借用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用自然主义笔法写暴力、写性,注重作品阅读的快感,对这些现象极尽夸张、渲染以刺激读者。
另一方面,九十年代以来,梁晓声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自我暴露自我剖析。在开始的时候,这是一种把心赋予给读者的真诚,然而随着创作中自我剖析成分的不断增加,它慢慢变成了梁晓声的一种标识,惯性甚至是表演。如《学者之死》中把“我”充当“穴头”向组织单位索要出场费写出来,这些对于情节无关紧要的自我暴露已失去了真诚的品格,掺杂了炫耀与卖弄的成分,索要出场费是为了给吴亮帮助,而在会场受到了奚落,这一情节反衬了众学者学术良心的失落,这一自我暴露以自我否定为开始,又以自我肯定终结,带有一点文人自恋的酸气。因此,梁晓声的平民化又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贵族的印记。
从梁晓声的后期作品我们读出他“似乎也秉承一种欣赏、留恋的态度而失去了那种针砭灵魂的光芒”,我们看到一个思想家的梁晓声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作为优秀作家的梁晓声,离我们越来越远。
结 论
梁晓声始终坚持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去感悟社会人生,尤其是九十年代后的底层叙事,面对已经逝去的青春年华和人间美好的感情,梁晓声仍旧一往情深。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我愿以我的小说,慰藉中国中下层人们的心。此时它应多些柔情,多些同情,多些心心相印的感情。另一方面,我愿我的小说,或其他文学形式,真的能如矛,能如箭,刺穿射破腐败与邪恶的画皮,使之丑陋原形毕露。”他对平民阶层的同情,对社会丑恶的愤慨,他的“为民立言”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与尊重。
在梁晓声的后期创作中,他为我们展示了底层人民在艰苦环境中质朴的感情,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面对人性的沦丧和扭曲,梁晓声执着与人生信仰、道德关怀的审视与探究,他用冷峻的笔调,展示社会不公及丑恶的一面,剖析着人性丑恶的根源,这些作品也不可避免要打上了作家和时代精神的烙印。
研究梁晓声九十年代后的创作,对于我们更透彻的探究理解其个人气质和文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纵观梁晓声后期创作中的底层叙事,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文本艺术的特色,都和作家坚守的平民文化立场和“为人生”的创作理念有着直接关系,由此所带来的意义及局限性同样令人瞩目与深思。
致 谢
对于论文的完成,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徐彦利。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每次有困惑不知如何下笔的时候,都是徐老师帮助我分析思路,给予了我很多专业性的建议,论文能够按照学校的要求如期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徐老师。由衷地感谢徐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感谢大学四年来,中文系所有老师对我学习上的帮助和生活上的关怀,是你们的教导让我收获知识,逐渐成熟。你们就像家人一样让我觉得亲切,正是你们的辛勤工作,才使我得以顺利地完成学业,取得学位。浓浓师恩,终生不忘。
感谢我的同班同学,四年来,我们组成的这个大家庭给予了我那么多的欢乐和感动,在学习和生活中,我们一起进步,是你们见证了我四年的成长,在大学这个美好的时光里,我们的情谊重重地写下了“青春无悔”。
参 考 文 献
1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34
2 孟繁华.梦幻与宿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34
3 徐中玉.伟大作家论写作.成都:天地出版社,1943,27
4 陈小明.永远的舞者——重新解读梁晓声.艺术评论,2004(8)
5 王向辉.商业时代的英雄情结——梁晓声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36
6 梁晓声.梁晓声语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163
7 高尔基.论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18
8 蒋建强.从人性温馨的理想主义到物化时代的严峻批判——梁晓声世纪末的女性形象表达.名作欣赏,2008(20)
9 陈国菊.寒门才女的无言之歌——梁晓声小说《贵人》意蕴解读.小说评论,2007(01)
10 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23
11 王莉,张诞松.当前底层文学的悲剧精神解读.当代文坛,2006(2)
12 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大学出版社,2002
13 池莉.我写《烦恼人生》.小说选刊,1988(2)
14 坷垃.在失禁的道德激情中作秀——梁晓声批判.十作家批判书.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