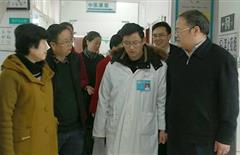中国古代文学对人与自然关系地描写
发布时间:2019-11-23 01:27:12
发布时间:2019-11-23 01:27:12
中国古代文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
2012级文学院四班 史雪平 学号
摘要: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的生存基础,它除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外,还满足了人的精神需求。随着人们利用与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加,中华民族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逐渐确立了为我所用的人本主义立场,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要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人们真正的长久生存的基础。古代中国没有建立系统的生态伦理观,但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却有许多。主要包括:人应该适当地节制自己的欲望,不应该过分的向大自然索取,尽量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人应该具有爱人之心,善意的对待自然界的万物,尽自己微小的力量去帮助弱小的群体;在满足自身生存的物质条件后,不应该无休止的向自然界索取,要做到给自然物以生长的时间,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而道家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而中国古代文人大都在青山绿水中积淀自然的灵性,他们在自然山水中释放自己,展示他们的诗性,这些青山绿水就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素材,无论是魏晋还是唐宋又或者是明清,自然界的万物在文人的笔下被描写生动而富有诗意。文人往往寄情于山水,在山水中洗涤内心的污浊。在花草树木中寄托性情,在从鱼鸟兽中体会生命的活力。
关键字:自然界 天人合一 和谐
人们对于自然地理环境审美功能的认识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原始社会和渔猎文明时期,人们的生存更多的依赖外部环境,自身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尚未得到有效的开发,中国古人对自然的认识亦如其他民族一样,曾经历过以神秘感应为核心的巫术阶段与神化自然的自然神阶段。在上古神话中,有大量描写人与自然是如何抗争的,比如:女娲补天、后羿杀群害,大禹治水等传说,这些无疑是在讲诉我们的原始先民在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的先进勇敢的事迹。
当人们进入农业社会时期人们的生产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也不像之前那样仅仅依靠自然界来获取食物,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从依靠自然界中完全解放出来,生活中还是需要大量的资源。在《诗经》七月中就描写了农奴们狩猎活动和采摘活动,如“一日之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在明清时期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还是能看到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向自然获取必要的生存物质。
在殷商时代,人们还普遍认为自然是由一个万能的人格神—帝或上帝主宰着。到了西周,人们虽依然保持着对天的虔敬,但已不像商人那样将天看成人格神了。周人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观点,他们在人事上更看重“德”的作用,天实际上被敬而远之了。春秋战国之时,士人阶层崛起。这是一个极富独立意识与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他们反思社会、反思自身,并且开始在哲学高度上思考天地万物的存在与意义。然而,由于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无固定地位士无定主。由于政治手段的匾乏,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反归自身—首先营构自身精神人格如儒家的存心养性、进德修业;道家的虚而静、适性逍遥,然后再设法将自身人格境界外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规范。这样的心态与企图就使士人阶层从一开始就不是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理解天地万物的,他们之所以对自然发生兴趣,完全是自救与救世的深层动机。因此士人阶层对天地自然的认识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阐释过程。就先秦而论,士人对自然的认识尚属一个笼统的、整体的把握。先民们只能以实用功利的眼神深思自然环境,但是中华民族始终没有站在自然的对立面他们继承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并没有对自然资源进行大量的索取。
儒家强调仁和仁爱,人应该要有仁爱之心,不仅要爱护自己的家人还要爱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且应当善待自然万物。孟子提出了“君子远庖厨”而佛教则告诫人们不要杀生。孔子告诫当权者说:“君子有三畏:畏夭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里的“君子”是指各诸侯国的执政者。他还威吓他们说,“获罪于天,无可祷也”。在孔子这里,“天”成了支撑个体精神以与君权抗衡的超现实力量。这里显示了孔子敬畏自然的心。在《论语》中“弋不射宿,子钓而不纲,”孔子本人钓鱼时只用钓竿,而不用大渔网:打猎时只射飞鸟不射归巢的鸟。这是一种保护动物反对人类竭泽而渔的向自然索取的方式。应该顺应自然尊重自然。
道家提倡道生万物,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构建与自然和谐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天人合一”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的,而作为这种广泛而又深远影响的最典型物化形式的便是中国文学中长期以来不断积淀而成的自然,出于对人类与自然的同体与共、亲和互融的合一关系的共鸣,中国文学的自然性就进了自然性,即万物皆是生命、皆是同胞兄弟,万物皆是一体的内蕴。而宋代道学家张载的“同胞物与”的思想则是对这一内蕴核心的最精要的概括。出于对人与自身天性自然的同体与共,亲和互融的合一关系,即人与自身天性的合一的共鸣,中国文学就显示了自然就是自由、自然就是人的精神和心灵的解放等。
人与山水的关系日常密切,自然界的万物在我国的先民的艺术创作中早已有之。战国时代的屈原在他的艺术创造中描写了大量的自然景物,并且富于了这些自然物人的品性,在屈原描写的香花芳草嘉木中,最能体现出屈原精神与美好人格的作品当数《橘烦》,它描写的是一种清醒的性格,一种端庄的品德。他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这正是屈原自己的品性。屈原一生的悲剧与这种对故土的爱恋是分不开的。他对幼橘尽情地赞美:“暖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拔,靡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他从幼橘欣欣向荣、青翠端正的形象中,认识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纯洁高尚的品德,一颗可以“塞于天地之间”的赤子之心。“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精神。“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认为只有讲究内心品德的修养,具有公正无私的品德,才可以“参天地”。橘颂既是赞美橘树的品德,又是借咏橘而自喻。这种借自然物来自比的艺术创作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物的喜爱。
魏晋时期文人对自然山水的关照度愈来愈热切,出现了大批的山水诗人,青山、绿水等意象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杨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池塘生春 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登池上楼》)正在于作者表现在大自然的美景的热爱才能写出这样美的诗句。“池塘生春草”这种展现自然物勃勃生机的画面使之成为名句。其它象“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过始宁墅》“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泽兰渐披径,芙蓉初发池。”《游南亭》这些诗中,“净”“明”“抱”“媚”“戏”“弄”“渐”“初”诸字,都恰如其分地渗透了诗人的感受,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情景交融”。谢眺的诗也同样。“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余雪映春山,寒雾开白日。暧暧江村见,离离海树出。”《高斋视事》“朝光映红萼,微风吹好音。”和何议曹郊游》“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和徐勉出新亭渚》。这些诗句都表达了诗人对自然中那清新,明丽的景象的喜爱,这种喜爱也感染了读者。这些对原生态自然环境的美的描写,既源于个人的现实审美感受,也是中国民族审美的艺术折射,也反应了中华民族对自然的独特体验。
崇尚自然的召唤使人们自觉的走向自然山水。人与自然关系一旦与隐居的生活方式或者只是一种企图结合在一起,便向日常生活的层面落实下来,从而完全包容并且超越了汉末曹魏及晋初的“悲情自然”与西晋及东晋初期的“玄想自然”,而成为一种既体现了审美主体自主性,又不抹杀自然物自在性的全新的“自在的自然”。和在诗歌中的情形一样,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和谢灵运的《山居赋》,分别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完成了辞赋当中的这一转变。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和他的诗一样,形象地展示了“自在的自然”,同时也是用文学的形式,表述了他对东晋以来玄学所关注的生死解脱、形神关系等问题的哲学思考。赋中所展示的,是全新的“自然”,其中充满着生活的情趣,淳朴天真,不加“矫厉”,一切都是“质性自然”地存在着。陶渊明“从他的庭园悠然窥见大宇宙的生气与节奏而证悟到忘言之境”。作者的生命体验与山林田野之间的本性相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自然的山水给人们的心灵以洗涤,“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招隐寺》。“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较书叔云》“凭高远登览,直下见溟渤。云垂大鹏翻,波动巨鳌没。”李白《天台晓望》“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间。”李白《赠裴十四》“一溪初入千花明,万壑度尽松风声。”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在李白诗中,即使是《蜀道难》,也不是造成恐怖,凶险的效果,而是瑰奇、豪放。《将进酒》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也不是压抑的、恐怖的。《观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们仿佛看到庐山瀑布飞泻而下的仙姿,这是一种真正神与物游的境界。
文人置身红尘,回归自然,歌咏自然,他们认为自然是纯净的没有染上城市间污浊,用自然中的植物来美化生活则是文人常用的笔调。“桃李罗堂前,榆柳荫后檐”《归园田居》。庄子回归自然的思想引导了大批文人士大夫将人生的目光投向自然山水因此苏东坡才写出了“宁可是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名言。
动物也是文人笔下对自然描写的重要对象,他们往往用超越现实功利的目光去欣赏动物,通过描写动物的声音、颜色、姿态,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与活力,“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春燕啄春泥“(白居易)通过构建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营造诗意的写作氛围。
古代文学作品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作家的审美心理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人比德于自然,意味着人对自然的欣赏其实就是欣赏人自身,特别是人所具有的精神品格。因而中国文学中的对山水(自然)审美观照,并不是欣赏自然本身的美,而是欣赏自己人格的高尚和完善,并以此作为人与自然的本质和意蕴。在他们眼中,万物都具有人格的意蕴,最高的美不在自然而是理想的人格,最高的美感就是对这种人格的体验。
中国文学中对自然的审美,其实质就是对自我人格的欣赏,人比德于自然的方式,事实上正是中国文学对自然最常见的感悟形式,人们常常以自然物的某种外在或者内在特征来自比。说一个人伟大、崇高,便是“重于泰山”;假如一个人低贱、卑劣、渺小,便是“轻如鸿毛”;说一个人沉着镇定就是“稳如泰山”;说一个人惊惶失措,就是“草木皆兵”,这些自然物象征着人们的某种品质,是中国人一系列的观念、意识、思想、道德等意蕴与自然特征的契合。自然的一切特征都和仁者、智者的精神品质具有类似性、对应性,都被赋予了丰富的伦理道德的意蕴,这样对山、对水的热爱和欣赏,事实上也就是对人的精神品质、道德伦理的热爱和欣赏,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有很多的文人雅士以描写自然、归于自然来表达他们的精神境界和对自然的喜爱与敬畏。总之,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大都是描写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从而反映了中国人们热爱自然敬畏自然的民族心理。
参考文献:
《自然地理学》 刘南威 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发生学研究》户晓辉
《空间与审美》周晓琳
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何西来.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因素
朱熹 诗集传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