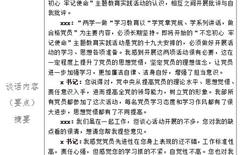故乡是这样消失的……
发布时间:2016-05-18 19:15:24
发布时间:2016-05-18 19:15:24
如同“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拆房队终于进村了......
今天,春雨潇潇,气温还有些寒意料峭,我开车碾着泥泞回故乡看孤单生活在那里的老母亲(老父亲因脑梗治疗后刚从协和出院,回乡生活诸多不便,暂时安顿在老三家,待天暖后再做长久打算)。原来进村的弯曲平坦的水泥路已经毁弃,路基刚被整直并拓宽数倍,还未来得及铺上石子和混凝土。春雨一下,新翻出的黄土被来来往往的车子碾过,形成黄褐色有粘性的泥泞,很难行走。到村后,看到村南数家房屋已经被拆,木料、预制板、砖、瓦及门窗等分名别类堆放好。被拆房的屋顶没有了,真正说得上是“徒有四壁”,且留下的半截墙壁被拆去窗户后留下的空洞,如同绝望的死不瞑目的眼睛。有的墙角或无窗的山墙也被胡乱打出园洞,透着凄凉的荒芜和空虚。据说,这样做是因为天晴后,便于推土机轻松推到墙壁而不出事故,以利于安全和提高拆房效率。
今天下雨,拆房队雨中作业不安全,故休息。春雨中暂时停止拆房的故乡,除两家在往车上搬家具有点声响外,沉寂一片,连鸡鸣狗吠都不闻一声。这是因为,房屋拆迁在即,家家户户都已将鸡鸭鹅等家禽宰杀干净,片羽不留;村里的十几条狗,已经被在“鸿门宴”上大出风头的樊哙的徒子徒孙三番五次游说,廉价收购而去,仅留下我家的叫“四喜”的小黄狗。母亲还在犯愁,过几天搬家了,人有着落,“四喜”怎么办呢?——家没有了,“四喜”何处栖身?
母亲介绍,拆房队都是四川人,十几个,男女都有,系庙山井村的小明所雇用。这群拆房的人都是职业拆房者,所用的大小工具简单易行,非常称手。男的负责上房揭瓦,下木料及预制板;女的在地面将砖瓦等码堆整齐,便于销售时清点数目。动作麻利极了,手脚并用,半天的功夫,一间完好的红砖红瓦房就如同“庖丁解牛”一样,被干净利落“分解”成砖瓦、木料及门窗,并堆放整齐;有意留下半截非常结实的山墙及墙基,打出园洞,只等推土机上阵,彻底从地球上“消灭之”。
拆房的程序是这样的:村里凡房屋补偿款谈妥且到位的人家,均被村小队长“狗狼子”(系诨名)反复通知:一周之内必须搬出,并被要求该房子的一砖一瓦与己无关,不得擅自处理;房中的家具衣物及其他日常用品可以搬走。接着,拆迁办视该空空如也的房屋的好坏优劣,论价卖给小明领导的拆房队。拆房队男女齐上阵,将拆房所得的砖瓦、木料及门窗、预制板,按质论价经拆房行业特殊的销售渠道卖之,所得款项作为拆房者的工钱及自己所得利润。这个庙山井村的小明何德何能可揽此生意?乃是因为其兄“幺伢”系本地一大佬级“头面人物”,可镇得住一方耳。
这一环套一环的拆迁程序令我想到非洲的大草原。那儿的弱肉强食和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疏而不漏地统治着所有的生物,大小生物都是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道法自然,秩序井然,所有动物种群都在动态的平衡与竞争中,迁徙觅食,繁衍生息。狮子捕食角马,吃饱血淋淋的鲜肉后安然睡去;饥饿的猎狗成群结队而来,在狮子留下的“残羹冷炙”上大吃一通,陆续离去;天上的秃鹫追腥逐臭地飞来吃掉腐烂的内脏和骨头缝隙中的残肉,也飞走了;地下的蚂蚁和其他微生物纷纷爬上角马支离破碎的尸体,继续蚕食余下的部分......要不了多久,一头活蹦乱跳的角马就变成了一付干净的森森可怖的白骨架.....。在我乡圈地拆迁所带来的利益链条上,谁是狮子,谁是猎狗,谁是秃鹫,我不得而知;有两个角色确凿无疑:角马就是那即将离乡背井的拆迁户(包括我家),蚂蚁就是眼前这些已经进村的拆房者。
母亲说,拆房的四川人很本分,总是天没亮就开始,一直干到夜幕降临,月亮上山才歇息。每天干活很累,人平可赚300元左右。晚餐时,到我家小卖铺买大量啤酒畅饮,谈笑风生,其乐融融。他们拆完东村拆西村,以此为业,信誉不错。该拆房队的人都很老实,只认干活,不管其余;如果有未谈妥有争议的房屋,他们一律不沾边;只拆那些铁板钉钉没有任何矛盾的房屋。
我在家门口碰到儿时的伙伴“七胜”——已经谢顶,满脸络腮胡,面目黝黑。他说,他家连房带披屋、院子,谈了四十几万,钱已经到位,天天被人追着,天晴就得搬家。新的住房已在豹澥镇租赁到手,先搬到那儿住一段时间。搬迁过渡费人均每月220元,根本就不够用;再加上目前要租房的人多,有房出租的人少,好些人拿着钱都租不到房,愁死了。听说豹澥小区安置房今年六月建成,何时可住人还是未知数。不过,搬进新房过年铁定不成问题。他说这些时,脸上不带一点感情色彩,透着麻木的无奈和驯服的苦笑。最后,他说:过两天就搬,搬出去就回不来了,......不可能回来了。语气里似乎含着不易觉察的凄凉,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味。
一会儿,邻村桂同方湾名叫“体伢”的来买烟。这个“体伢”1958年生人,比我大五、六岁,小时候经常跟他一起放牛、砍柴、扒树叶,关系不错。因该兄儿时很调皮,经常打架闹事,前后湾流传一段关于他的儿歌:体伢体,纳鞋底/纳几双,纳三双/纳给体伢过端阳。眼前已经做爷爷的“体伢”枯瘦如柴,脸上皮包骨,牙齿稀疏,嘴和下巴如同列宁一样向前翘着。吸烟时,眼睛眯成一条缝,很是享受的模样,似乎日子过得很滋润。一开口就说:小时候我吃了几多苦啊!读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什么脏活累活没干过?好不容易,养了三个儿子,建了两栋房,现在又要老子搬家!马上就得搬,一天都不能等。两栋大房子谈了八十万,不算蛮多(说到此处,脸上有点掩饰不住的自得的笑意)。我得保证每个孩子有120平米的还建房啊。现在,两个孙子在身边,我养了儿子还得养孙子......我过度的房子租好了,天晴就走人,干干净净,走了就不回来。......狗日的,这个地方,看都不值得看一眼,连尿都不朝这个方向拉......。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恨生他养他的故土?莫非,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爱?
吃午饭前,母亲要我到黄金堂去打点货——米、面、香烟及副食类,供应给拆房队及附近的建筑队。我和老五驱车走在已经破残且泥泞不堪的乡道上,放眼望去,全是村庄被拆除后留下的一马平川的空地。稍远处是繁忙的工地,远远地,可看见成排的彩旗在春风中飘舞。昔日所熟悉的大张村、大杨村、姚蔡村、葫芦村及更西边所有村庄,均消失了,连残垣断壁都看不见。每座村庄四周大片的田野和树林也不见了,到处都是被推土机新翻的土地。大小树木一律砍伐放倒,那些还没长出叶子的大树上的鸟巢及巢内的羽毛散落在泥土上;被推土机翻出的树根,有的碗口粗,有的小指细,全纠缠在黄土堆中。新平整的土地中央,建有一排排蓝色的工棚;不远处是脚手架和安全网包裹着的比春笋长得还快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雨中,工人们和塔吊仍旧忙碌着。
紧靠路边是小张村拆迁后的废墟,大部分已经被红褐色新土盖压;在未被新土遮盖的残余墙角,还看得见石磨,瓷盘瓷碗及装咸菜装油盐的小陶瓷坛子,均被主人弃之。乌鸦和麻雀在这片废墟上飞起飞落,似乎在寻找筑有巢窝的树林。这不能不让我想起陶渊明的诗句——羁鸟念旧林,池鱼思故渊。不远处,有一片茅草地没有被新土覆盖,那茅草呈灰白色,随风起伏。再过去一点,是父亲读私塾的范道士村,该村仍处在暂时的安宁中,没有被拆房队所侵扰......
打货毕吃午饭时,母亲说:全村几十户人家,只有五户没有谈妥,悬在那儿,其余的全都签了字,钱也到位了。这些拿了钱的人家,下周内必须全部搬完,一户不留。有的人说池塘、祖坟山、大路及水渠的土地补偿钱还没有分,不能轻易离开。这是最后一把“草”,村里人人有份。看样子,抗不住,非走不可。
至于还没有谈妥的五户人家,马上得谈,越快越好;拆迁办说是现场办公,今天签字今天的钱就到位,要现金就现金,要金卡就金卡,一天也不拖,悉听尊便。说是这样说,我家的房子就没谈妥;不为别的,就是无人来家谈,凉在一边不理睬;我们兄弟几个在家苦等数次,不见一人来上门。母亲说:不知为什么?全村就我家的房子无人问津。昨天,村书记胡某某打门口经过,还半讥讽半威胁地说:老婆婆怎么还不搬家?你家的钱多得很,要什么补偿,就那样拆了去鬼。再就是前几天,送来900元钱,说是我家房屋前屋后的树木补偿费。并发话:拿了钱,房前屋后的一草一木都无权处理,公家买走了。我笑着说:他不来谈,那很好,我村因依山面水是规划中的别墅建设区;我家顺坡下驴,直接改建三栋别墅算球。至于300元买树木的事,那是霸王条款,不予理睬。老子家那么多参天大树、大竹林,你丢下300元全买走,天底下有这样的买卖吗?你这样霸道,有王法有天理吗?万恶的旧社会都无此先例!母亲听后哈哈大笑。
听说,高新开发区的钱已经到了九龙村,只要这几户人家谈妥了,本村的拆迁大任就算功德圆满。拿到补偿款的乡亲们将四下寻找自己的栖身之所,自己负责今后的人生......
无论怎样,有一个事实冷酷地摆在全村人面前:还有一个月,一个已存在600余年,生我养我,名叫郢家岭的小村将在地球上彻底消失,仿佛从未有过似的......
鲁迅先生曾说“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他若看到今天的情形,不知会发出怎样的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