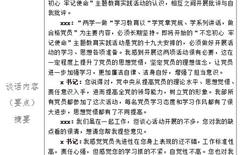李白杜甫白居易乐府诗之比较
发布时间:2018-06-30 13:29:08
发布时间:2018-06-30 13:29:08
李白杜甫白居易乐府诗之比较
唐代乐府发展史上,李白、杜甫是两个重要的转变性人物,李白既承上又启下,杜甫承之,直写时事,使乐府方向变化转型。李白乐府诗正多变少,杜甫乐府诗正变相半,迨元稹、白居易等人,已然大变。
“青莲集中乐府累累如贯珠”,李白是唐代写乐府诗最多的诗人,李白擅写古乐府而知变。其乐府“根植《风》、《骚》,驰驱汉魏”,“多有古辞”,“绝类汉魏”,又“无一语似汉魏者”。
李白在乐府中运用讽兴手法的诗更多。李白乐府秉承《风》、《骚》旨意,多兴讽当时君臣国事,如《上之回》讽明皇好神仙;《战城南》“刺黩武而戒穷兵者”;《幽州胡马客歌》刺天宝十载安禄山败于契丹等。李白较前人同题作品,诗歌容量体制扩大。李白依古题立义且变古词。这不仅体现在内容的变化,而且体现在句法的灵活多变,结构的跌宕起伏,及对古题意的新发明。内容上,李诗能学而不泥,变化前人。李白乐府能突破汉魏六朝乐府的句法形式。擅长结构变化多姿,文脉跌宕起伏。无论是《行路难》起伏多变的心路历程,抑或《蜀道难》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反复歌咏、一唱三叹、逐步深化,还是《鞠歌行》始伤士不遇、中羡昔贤遇合、终叹今不识士交自况,皆为确例。
赋法讲究铺排,李白常引之入古乐府。李诗意象较稀疏,上下句或者前几句往往都是叙说一个中心,不像杜甫诗歌中意象密集,头绪纷繁。李诗读起来更有一种悠扬之感,似乎难给人细细品味思考的时间。
诗体上,李白有五言长篇,杂言歌行,七绝,五绝,五律等。杜甫新乐府多为歌行。内容上,李白诗颂美兴讽、边塞战争、闺怨思乡、叹世自放、送友求仙等,杜甫诗基本皆写战争。尤其李白《塞下曲门首》昂扬健举,透露出盛唐气象,而杜诗多写安史之乱,从正面战事、王孙宠妃、征夫其苦战等方面叙述,更贴近现实,较之李白更进一步变化了乐府。
李白上接汉魏,“文质相炳焕”,杜甫继承前人,又学习李白乐府的新变,自创乐府新题,洞开中晚唐新乐府之门。李白集大成而知变,杜甫更变李白为新。杜甫乐府诗在体裁、题材、形式、技法、神理、叙事、议论、兴讽等方面,多学习嬗变李白乐府诗,可以说杜甫是李白古乐府对中晚唐乐府新调转换的津梁。
总揽李白乐府,众体兼备,尤擅歌行,题材多从军边塞,杜甫亦然。至于李《蜀道难》、杜《兵车行》之创体,如出一辙;李杜皆学古不泥并知变,李白乐府法汉魏万墨,“所拟篇幅之短长,音节之高下,无一与古人合者,然自是乐府神理”。杜甫无论教子要熟读《文选》理,还是自己创作乐府诗,皆重取其神。究其然,李杜乐府渊源归一也。李白乐府多兴讽,喜借古题写时事,李、杜皆擅兴讽,前无古人。李白乐府诗多刺时事,且符合温柔敦厚之旨,如《丁督护歌》“落笔沉痛,含意深远,此李诗之近杜者”,正同于杜诗儒家思想外化而呈现的特点,实启白居易新乐府讽时先鞭;李、杜乐府皆擅写组诗,文脉贯通一气,跌宕起伏多变;李白乐府好发议论,形式灵活,多置句尾,杜诗议论渐多,新乐府“卒章显其志”,更为程式;李诗如《野田黄雀行》第三、四句分别绍述第一、二句的诗歌错置手法,也是杜甫善用的;李乐府诗借用汉大赋主客问答之法,这对杜甫、白居易等新乐府的问答法,赋法有影响;李杜皆擅虚字入诗,擅措谚语、成语、歌谣手法入诗;李白古乐府诗常借古喻今,以秦皇汉武喻唐,杜甫亦然,如《兵车行》等;李白乐府诗中常有第一人称出现,而杜乐府诗中也有不少,如《逼仄行》等。
当然李、杜乐府还有很多不同,“李、杜乐府皆有所托意而发,……但子美直赋时事,太白则缘古以讽今”,“直赋时事”即指杜甫的新乐府而言,虽李白也有“开元、天宝本纪在内”的诗歌,但相比之下,杜诗史性更明显;李白乐府诗飘逸奔放,行云流水,一唱三叹,无法度而从容于法度之中。杜诗则“词取锻练”,“悲欢穷泰,发剑抑扬”,“壮丽结约,如龙骧虎伏,容止有威”。
在盛唐诗坛上,李白和杜甫都写了相当数量的乐府诗歌,堪称乐府大家。李白乐府诗的主要成就在拟古乐府,杜甫则更擅长创制新题乐府。在乐府诗里,李白擅长主观述怀,杜甫擅长客观写实。尚虚与尚实,正是李、杜诗歌创作方法上的主要区别。同时也使得他们的乐府诗呈现出不一样的境界和风格。
以李白的乐府诗《远别离》和杜甫的乐府诗《丽人行》为例,分析他们在各自诗中表现出来的“虚”和“实”。
李白的《远别离》一诗,实际上是影射当时的时事,是确有所指的,即借舜妃娥皇女英的故事来劝诫明皇不要以国柄轻易授人,忧虑君主有“龙为鱼”之患,权奸小人有“鼠变虎”之虞,但诗中不好明言,所以就把此意化为舜妃娥皇女英的故事。诗歌表面写虚,但却处处虚中有实,即“以虚写实”。
杜甫的《丽人行》一诗,也是写当时的时事,即讽刺杨国忠兄妹的荒淫奢侈。但他并没有像李白一样隐约其辞,而是对一个生活片段进行了严格的写实,几乎不用任何比兴手法。不论写丽人的姿态服饰之美,还是写她们的饮食之精,都是客观冷静的白描,不动用任何手法拐弯抹角,而讥讽之意呈现无遗一。尽管用一句隐语“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含蓄地揭露杨国忠的丑恶行为,但丝毫不能左右全诗的写实情境。和李白的“以虚写实”不同,杜甫是“以实写实”。
李白诗意旨多模糊,指向多不明,现实针对性较弱;杜甫诗意旨多清晰,指向明确,现实针对性很强。
李白的乐府诗多是一些感事之作,很难去对应当时的历史现实,这和杜甫乐府诗“诗史”的面目截然不同。他的这些所谓的感事之作,在表现手法上,以借助想象感怀的居多,写实的甚少。有时即便写实,在旨意上也往往显得迷离惝恍。最典型的如《远别离》,借舜妃娥皇女皇的故事来劝诫明皇不要以国柄轻易授人,用“舜帝囚禁尧帝,后又被禹低所逼,出走于苍梧之野”这样一个传说中的悲惨故事来暗喻可能上演的篡位夺权之悲剧。这样,一场政治危局被诗化为一种迷离恍惚的幻境,而这种幻境又浸染了凝重的绵绵哀愁,使诗在情调上显得更为哀郁。有的反映时事的乐府诗,也写得隐隐约约,像《上留田行》一诗则在暗示我们:兄弟之间为了争夺国家政权,竟然动用了兵力去互相残杀。不难看出,这首诗是在借上留田的故事来指涉讽喻时事。《丁都护歌》虽是借乐府旧题来咏时事,不用比兴手法,完全写实,但就像杜甫的《兵车行》一样,没有写清背景是什么。但它的主旨是明确的,即同情劳动人民的艰苦劳动,刻画天热热水旱时的拖船,万仞享凿磐石的辛劳。《蜀道难》用各种夸张比喻的手法来写蜀道的艰难,但其真正所指却众说纷纭。
和李白不同,杜甫的乐府诗大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主旨也比较明确。杜甫写下了有名的‘三史’、‘三别’。杜甫的诗歌,不但为后人提供了鲜活的历史史实,而且提供了比事实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杜甫将他博大深沉的忧国忧民意识熔铸在对现实痛苦客观冷静的陈述中,使其乐府诗具备了“诗史”的性质。李白的写虚与杜甫的写实,造成了他们乐府诗风格和境界的不同:李诗“飘逸”,杜诗“沉郁”;李诗“惝恍莫测”,杜诗“恳恻如见”。
杜甫继承李白诗歌,杜甫赞李白诗歌因为常创新,故卓然不群,技压群雄。《雨村诗话》云:“不似称白诗,亦直公写照也。”道出李杜诗歌相似处。结句杜甫渴望能再次与李相遇,把酒细细品论诗文。《少年行》是李杜题目字样完全相同的唯一乐府诗,《杜诗镜铨》称杜该诗“略似太白”,同样看出了杜甫对李白乐府诗的学习借鉴。
因安史之乱,杜甫上取风雅汉魏,并直接继承李白乐府,而写出了具有杜甫特点的写实叙事乐府;李白乐府主于意,是白居易新乐府“系于意不系于文”理论的开启者。
从汉乐府起,就继承了《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大多以叙事的手法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状况。直至中盛唐时期,杜甫自拟新题,“即是名篇,无复依傍”,真实再现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全景。诗歌发展到元白时期,白居易取儒家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新乐府。之后,白居易大量创作新乐府诗,形成自己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都力求做到讽喻美刺,言真而切,继承着“温柔而敦厚”的传统诗歌精神,而又对其进行着超越。
白居易主张“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一语道出他诗歌的政治功用之所在,但杜甫对于百姓疾苦的描述与反映仅限于诗歌,并没有上升到诗歌理论。直至白居易才明确提出诗歌创作一定要“惟歌生民病”,并且诗人也始终恪守着这一创作原则,为百姓喊冤,为生民控诉。诗人在生活中饱含为民的满腔热情,并时时用锐利的眼睛洞察世间不平,进而用诗歌代其口指斥时政弊端。如《卖炭翁》,诗人通过起承转合的简单叙述,将一个卖炭老翁的无奈与困苦,鲜明地展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从诗中我们都看到了“宫市”制度给人民造成的极大痛苦,也深刻地理解到这种制度的罪恶。从字面意思我们不难看出“宫市”表面上皇帝派出太监到街上去买东西,但从诗中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我想我们就会知道这种“买”无异于抢。白居易正是捕捉到了这种个别的场景,寓特殊于一般,描述了如此遭遇的广大人民,揭示了“宫市”制度之陷民于水火。
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是杜甫最忠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杜甫所开创的写实的精神,绕过了大历诗坛对形式的追求,到元稹、白居易的时代才进一步发扬光大。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诗学观点的传承。杜甫以后,也有一些诗人继承其变新的余绪,“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对白居易新乐府运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诗歌要写实、要讽刺的主张到了白居易有了更加明确的阐发。他说作诗要“但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总而言这,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作为文而作也。”并且明确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些都与杜甫的诗学观点一脉相承。
白居易评论杜甫诗,也是从写实的标准加以裁定的。白居易在创作上继承杜甫写实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乐府诗的写作。杜甫一贯重视运用乐府体裁来反映现实生活。杜甫以前的乐府诗,一方面继承《诗经》及汉魏乐府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又即事名篇,自创新题。杜甫的文学活动对中唐时期的白居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他写了很多新乐府、古题乐府等更加创新的诗篇,极大地发扬了杜甫新题乐府的精神。
白居易在《伤唐衢》诗中,说明了写作《秦中吟》的目的:“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明显是要表现民病,以及引起民病的各种政治、社会弊端。他在写《新乐府》时,更是与杜甫的新题乐府一脉相承,而且将杜甫的即事名篇精神进一步发展,以成为讽谕诗。
正因为如此,他才极力推重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石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诸章,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诗句。白居易的乐府诗,如《秦时吟》中的《轻肥》、《买花》,《新乐府》中的《道州民》、《杜陵叟》、《卖炭翁》、《缭绫》等,与杜甫诗一样,注意表现劳动人民的辛劳与困苦,而且强调作诗时特别需要核实,与现实生活靠近。
当然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特色,我们既要看到其“为时”“为事”的人民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平俗浅易的一面。
李白、杜甫等以乐府诗歌的实际创作,而显示出乐府发展演变方向,但并无理论总结。元稹、白居易继之,提出新乐府理论并进行创作。总之,盛唐李白为古乐府集大成者,是“正宗”;杜甫学习李白乐府而半变,系“大家”;白居易由杜入李而大变,是“正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