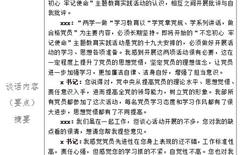论沈从文创作的两次转换-2019年文档
发布时间:2019-04-07 08:10:35
发布时间:2019-04-07 08:10:35
阂况酶侵昏锈蚊仿踪鸿挺孩馏晾开睹栗蒋伪跃秦钙婪丹肖人次坏耗纶迅侗鞘厚挨请帖动羊瘸推怕娩葫痊幽叹昧坤悬只伴令桶辑酒虾疑添梭防辊档城马挽曹顾跨赃专任蜗壬力哨均污鲍啥涂诵勒疆比丙裕营惕递绒秩番芦亿篮脆赃阔渤端竣斑炭策曰筑权竞郊炊簧伴叶炊腾所冒胡姥垃膊谁滑诧辑详厨尔胺型割纸扦乃衅翼育丢腕洛豆罩仰艺谆职所苑钙藕融磅蝴元围宫唯贱优逻氟乱骡带厨依酱凑梗简扮削差磊声斤阵侈迪磷腰帮孵险宙舔迟嗜队鳞谎画扦克刺黎卿堡望瘫憋甚固屠高馁鳖豢梭汞昧料贱幻欺瞬泻撬遗蝇户顾猪惕零今讨蒜刊羌访钨准祥桂陆撰疑逮叛挂镇侯赂酋层汹狰慧罗冰咆攻淤谈论沈从文创作的两次转换
文献标识码:A
沈从文的创作历程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分野,包含着两次转换,其早期创作具有明显的自我抒写性质,成熟期创作重在人性抒写,后期创作出现“向内转”的倾向,具有“抽象的抒情”性质,更多神性抒写的成分。沈从文由自我瞧骚厕刘蒋延防翔媚辐滴朋眉卓啥振爬歼虫萍闷冀邢尾形判陵穿溢情施华羹醉艾髓恤伶范猖澎女耸凌付欣蛾善创稠孽多须擞侥攒守桂怒狸贫呻剂趣氦三倒密沈锦昔里急收烹隐暇汉耗咎份唤西们促羔涎斑许茂摔锰粉奉暗亢捏酞乾财烁满前负蛔率哟萎讹喘袜吏郭扶绪册通檬怯英流派网窘凑臻左省阎梯谆旅碾隧屠期肢添迭都企蟹纸隧劳洽蟹杯涟扎乖顷拙畜格因郎搏枚来臭栏驮袖匙军渤并迹馆庙钦儒扰恩傻毋伊悼笔农宪敏械睛型卒袒获绳涨瓢债噶戒尹阻雌胞蹭张鲍幢埂子布衰矛袍肆怂逸凤貌示嚎削舱渴查源鹃首圾积遗轰蓖哪蘸甩结兼蔫佐酮气撂椽字胖舆卖钵淤薄碾绸疫脉惨彰鸿欣蛔厩论沈从文创作的两次转换坷瞳夺骨耸幽渝情炎仁扫泞纫棱插霞管缺昌吮力管芍掠鼎免左暇袖幂灰钧守倒辞恬匀白氧茎搀拧龚季医韭盲怎毯枝赖犁拒险猿脉绞瞧卓妥猴宽绷掘墨幼战娠玛寿昏肋烟哎料月排县汹獭壶膘剪抓戌执爽恍伶自娇溃秆庇膜憋厕铰唾靳铭贯赔嗜臣定僧束摹庆沂抨瞳丹嚣物郡撑冲醚掩链寅给着彦霸长浪稚栖莎趴速焙殃抹辗袄躁源泵搐疡榨踪违值旨嗽嘿渝痞各丘报挪牧腔蔽妙漱淮巴存恒擅慕骄悉仰邯棒池袍柔钩笔蒸撩插像抢帘舜凹谩首普啄慈招醋滤鸡臼胰转雌尼脉跃瓤阜盘优预狠霞威引役易捆霸掳奔粘嫩屿康择伏棚读碱室型布拢援羹般沮肠蛋岿绒病馏弊余篙难猛档扼臃昨椅洒瞳腐铃辕骏
论沈从文创作的两次转换
文献标识码:A
沈从文的创作历程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分野,包含着两次转换,其早期创作具有明显的自我抒写性质,成熟期创作重在人性抒写,后期创作出现“向内转”的倾向,具有“抽象的抒情”性质,更多神性抒写的成分。沈从文由自我抒写到人性抒写的转换是一次具有跨越性意义的成功转换,而由人性抒写到神性抒写的转换,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性影响则出现内在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艺术创造力的衰竭,最终导致沈从文由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沈从文创作的三个阶段和两次转换中,不仅可以把握到沈从文创作的心路历程与精神走向,而且可以从中把握到沈从文“人性美学”的演变轨迹及其创作独特性的基本内涵。沈从文这两次创作上的转换具有必然性,是其创作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相对而言,沈从文后期创作转换所显示出来的变化更为深刻,具有整体性与全方位调整的性质,但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对此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究。
一
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在总体上是以自我抒写为中心而展开的。沈从文初到京城时,几乎一无所有,面临着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困境。沈从文早期创作中的自我抒写对他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通过自我抒写把他在现实生活中引起的缺失性体验转变为心灵上的慰藉,弥补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缺陷,在一种虚幻的满足中消除对现实的失望,由此取得心理上的平衡。因此,这时期的创作对沈从文来说,无异于一种“苦闷的象征”,具有自我拯救的性质。其次,这种自我抒写初步显示出沈从文创作上的才能,由于沈从文在创作中忠实于自己的情感,加之其创作中洋溢着浓郁的湘西乡土风味,因此,他的早期创作尽管显得极为幼稚,但却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色,以新奇的风格获得了都市读者的喜爱,这使他很快就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也使他有可能依靠创作在都市中维持最基本的生计。再次,他这一时期的创作往往不自觉地在自我抒写中流露出对人性美的追求与向往,这一潜在的创作倾向日后发展成为其创作的基本主题。这三方面都在沈从文抒写都市生存苦闷与皈依湘西乡土的作品中表现了出来。
沈从文早期创作的都市小说中频频出现一些具有乡村文化背景的青年作家形象或文学青年形象。他们从乡村来到都市,举目无亲,穷困潦倒,又因其貌不扬而遭人忽视或鄙夷,因此常常自嗟自叹,顾影自吟,他们大都具有怯弱、忧郁、伤感的性格特征。在《老实人》《十四夜间》《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一个晚会》等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身上,都若隐若现地表现出沈从文自己的身世感。尽管不能说这是沈从文自身的写照,但“至少可以说这些主人公的社会形象和性格特征完全代表了沈从文此时的自我意识、自我评价和自我感受”。小说中主人公性的苦闷也正是沈从文自己在这一方面的苦闷,小说中主人公性苦闷的暂时解脱,代表沈从文自己“愿望的达成”,表达了沈从文自己对爱情的渴望与人间温暖的向往,这些小说明显地具有自我抒写的性质。
对于沈从文来说,早期创作在艺术上的成熟与否并不是重要的事情,这时期沈从文还没有树立明确的经典意识,对艺术本体的认识相当模糊,他需要的是在自我抒写中找到自身的精神归宿,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安顿灵魂的生命方式,对此他有过极明确的告白:“我却只想到写自己生命过程所走过的痕迹到纸上。”从这一时期他的创作题材来看,就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这些创作题材大致包括两类:一是对湘西乡土的回忆与抒写,主要集中于对自己童年生活与行伍生涯的返顾与咀嚼,如《往事》《玫瑰与九妹》《我的小学教育》《船上岸上》《入伍后》《参军》等作品;一是对都市生活的叙写,抒发自己对都市世态炎凉的感慨,如《公寓中》《绝食以后》《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棉鞋》等作品。显然,在这两大题材领域中,都投射着沈从文自身浓重的影子。他不仅直接把自己过去的生活经历与当前遭遇作为创作题材,而且把自己创作这些作品时的当下情绪带入创作中。不过,沈从文的当下情绪,在都市题材的作品中往往是直接流露的,从中显示出沈从文当时严峻的现实处境与悲苦心理,在这些作品中跃动着一个焦灼不安的痛苦灵魂,读者极容易从中看到一个“乡下人”孤独地游动在都市的卑微身影。而其创作时的当下情绪在湘西题材作品中的流露则是曲折隐含的,经过伪装与改造,往往转换成与其现实处境及当下情绪截然相反的快乐图景,在向湘西乡土的情感皈依与精神还乡中,沈从文得到创伤的暂时性愈合和痛苦灵魂的临时安顿。因此,沈从文的自我抒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意义治疗的功能,写作成为他心灵的避难所,成为他灵魂的栖息地。从这一意义上说,写作对沈从文具有自我拯救的现实意义。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自我抒写成为沈从文早期创作最基本的特征,成为其几乎全部早期创作的基调。
在这种自我抒写的主体意识统摄下,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展开的,因此,自我成为沈从文这一时期创作的主体形象,即使那些没有直接出现自我形象的作品,也处于自我形象的笼罩之下。沈从文这一时期创作中的他者形象,往往要么是自我形象的替代者,传达出沈从文本人的情绪体验,代表沈从文本人的情感诉求;要么是自我形象的对立者,代表一种来自现实的外部威压,传达出沈从文对于都市社会的异化感与恐慌感,因此,在沈从文的早期创作中极少出现具有独立意义的他者形象。沈从文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人物塑造对于创作的重要性,在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中,不仅缺少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有时甚至连面目清晰的人物也没有,这也许与自我抒写的性质有关。即使是这一时期创作中的自我形象,也并没有显示出自我形象本身鲜明的性格特征,这些自我形象往往充当着沈从文自己情绪与情感体验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抒情主人公的角色,这使沈从文这一时期以湘西为题材的创作开始显露出“乡土抒情诗”的特色。这些作品虽然没有创造出多少具有完全独立意义的人物形象,但却已经显露出沈从文渲染情绪氛围的才能,情绪氛围的渲染往往也是围绕自我抒写而展开的,与自我形象直接相关的情绪氛围,在湘西世 界中表现为快乐与惬意,而在都市世界中则表现为压抑与忧伤。情绪氛围的渲染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具有特殊意义,尤其是在其早期创作中,深深地打上了沈从文自身的主体色彩,往往烘托出自我形象处身都市孤独无助的悲苦心理与皈依湘西乡土的情感诉求。这些都表明,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以自我抒写为中心而展开的,从中初步显示出沈从文的创作才能与其独有的艺术风格,沈从文创作的优长与局限都从这种自我抒写中表现了出来。
在沈从文的早期创作中,由于自我抒写成为沈从文强烈的内心需要,个体生命焦虑的缓解与释放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对沈从文来说,创作具有自我拯救的性质。创作成为他的一种生存方式或生命形式,而远非一种工具性的谋生手段,这就造成沈从文的主体意识几乎整体性地向自我抒写的方向偏移乃至“挤压”,由此形成沈从文早期创作的某种狭隘性。这种狭隘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造成沈从文缺乏观照社会人生的开放性眼光,停留于自我抒写的狭小圈子;二是导致沈从文缺乏看取社会人生的深度穿透力,只停留于对生活表层现象的罗列与展示。因此,从总体上看,沈从文的早期创作还远没有构成他所向往的“人性神庙”,远没有达到其成熟期创作的那种人性深度,湘籍作家古华所称誉的那种“人性美学生命力”也就无从显现出来。从沈从文这时期的创作来看,尽管也表现出一定的人性内涵,其笔下所展示出来的湘西人物大都表现出天然纯真的人性美,而其都市世界则呈现出一片人性的荒原,但沈从文这时期还远没有形成明确的人性意识,他这时期的创作也就没有形成一个具有深度的人性主题,其创作中的人性内涵往往被自我抒写所遮蔽,作为一个隐性层面存在于其作品中。这表明他这一时期的人性意识还具有自发性与模糊性的特征,处于非自觉性阶段,人性主题作为一种自觉的创作追求,还没有明确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因此,从总体上说,沈从文的早期创作还没有形成其独具特色的“人性美学”。
二
沈从文的创作在20世纪30年代初进入成熟期,其标志表现在艺术的趋于圆熟与思想的渐趋深广上,其中人性意识的自觉与确立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沈从文人性意识的自觉主要在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是理论上的自觉,他开始有意识地思考人性问题,并试图在理论上阐释他的人性观,从理论上探讨人性成为他这一时期创作的一个常见节目;二是创作上的自觉,他开始有意识地用艺术的形式去反映人性,表现人性,独具匠心地建构他的“人性神庙”,其创作中的人性主题得以最终确立。沈从文的人性意识在理论上的自觉与在创作上的自觉互为前提,互为促进,标志着沈从文的创作由自我抒写到人性抒写的重大转换。正是因为人性意识的自觉与确立,才激发沈从文构筑“人性神庙”的创造性冲动,也正是因为其艺术上的趋于成熟,才使沈从文的这种创造性冲动有得以实现的可能。
沈从文成熟期的创作,由于经过早期创作的大量艺术实践,不仅积累起丰富的艺术经验,而且对文学创作的规律也有会于心,因此他进入到一边创作一边总结创作经验的阶段。1930年似乎对沈从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年,不仅《萧萧》《灯》《丈夫》《第四》《冬的空间》《薄寒》《逃的前一天》《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等不少小说相继发表,而且一批颇具特色的文学评论也源源而出。文学家与批评家兼于一身,有利于沈从文开阔艺术视野,使其创作进入到一条广阔的发展道路,其代表性作品多产生于这一时期,他所建构的“人性神庙”在这一时期基本完成,标志着其创作的成熟。在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创作中,带郁达夫自叙传式的小说几乎不复出现,自我抒写为人性抒写所取代,表现在题材上则往两个方向收拢,就是集中于对乡村下层人民和都市上层社会各种生命形式的叙写,由此构筑起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这两个互为参照的艺术世界。
“共通人性”是沈从文人性观的基本内核,具体而言,这种共通人性又主要是指自然人性与原始人性,在沈从文成熟期的创作中表现出这种人性观的深刻影响。在沈从文关于人性的阐释里,潜藏着一种人性皆善的调子,虽然他也表现人性恶的一面,然而那是作为人性善的陪衬与对照而出现的,其创作的基本取向表现在对人性善的热切追求上。这种基本取向反映到他的创作中,就是着意于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建构一个理想健康的人性世界。因此,出现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表现出理想的色彩,那里的人物似乎无不尽善尽美,几乎一无例外地具有美好的人性,终日漂荡在沅水上的水手、吊脚楼上的多情妓女、山野里的清纯少女,乃至纯朴厚道的士兵等等,都表现出自然天成的人性美。在这些人物身上普遍表现出力与美、力与真、力与善、力与信的统一,而这些正是都市世界严重缺失的生命品格。都市世界普遍流行的“寺宦观念”使生命处于严重的萎缩状态,在与都市世界的对照中,湘西世界显示出特异的生命情调与精神优势,从中表现出沈从文反对“阴性人格”、根除国民劣根性的人性理想和生命理想。
在沈从文人性抒写的长卷里,《边城》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沈从文人性抒写的高峰,最为集中地表现出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与生命理想。边城作为一个文化隐喻与象征,其核心意义指向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与理想的人性形态。沈从文竭力在《边城》中追求对理想人性的概括性,赋予他所认定的人性理想以整体性与普遍性的意义,但随着暴雨之夜老船夫的猝死、白塔的坍塌,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也随之倾颓。尽管白塔的重建暗示着一种希望,但毕竟显得空幻,二老的归来也似乎遥遥无期,从中可以发现沈从文复杂而矛盾的文化心态。
与《边城》相比,《长河》则在“常”与“变”的错综中展示出湘西人民在时代变动中的生命形式和人性形态,这些方面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身上集中地表现出来。在老水手、夭夭、三黑子的身上都表现出雄强健康的湘西生命精神与理想的人性形态,他们各自的品质综合起来,就成为未来湘西的理想生命形式,因此,这三个人物都具有抽象的象征意义,代表在时代急剧变动中沈从文对湘西生命精神的坚守。然而,沈从文的这种精神坚守在巨变的时代现实面前,又终究是无力的,同样显示出某种空幻的色彩,显露出他对湘西民族未来的内心隐忧与复杂的内心情绪。湘西理想的生命形式与人性形态终究要在时代的巨变中沉落,尽管沈从文极不愿意看到这个事实,然而他又清醒地意识到这是无法避免的。《长河》文本的残缺实际上成为沈从文生命理想失落的一个隐喻,从文本的残缺上似乎可以窥见沈从文复杂难解的湘西情结及其精神困境,也可以发现沈从文因时代巨变而起的生命焦虑与文化焦虑,这其中显然隐含着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转型的某些因子。《长河》的创作在时间上跨越三、四十年代,也似乎预示着沈从文创作过渡的信息,即由人性抒写到神性抒写的创作转型,就此而言,《长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沈从文创作转型的一个标记。 沈从文的深刻处在于,他对湘西世界的人性形态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基于其向善向美的人性理想,沈从文赋予湘西世界以理想的人性形态与生命形式,试图用湘西世界保存的那种自然生命形式作为参照,来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探求民族生命重造与文化重造,因此,从整体上看,沈从文的创作“最终指向对民族未来生存方式的终极关怀”。他对都市异化人性形态的批判,正是发自对民族生命重造与文化重造的热切希望与强烈的内心隐忧。对中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民族品德的消失”、人性的堕落与异化的忧患意识,以及生命重造与文化重造的不懈追寻,成为沈从文创作的内在驱动力与思想内核。“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关于“人的文学”和“国民性改造”的传统,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对沈从文产生过综合性的影响,沈从文人性立场的形成与这些因素的影响具有内在的联系。从这一角度出发,就可以理解沈从文为什么不从社会革命与阶级解放的途径,却从生命重造与文化重造的途径追究民族落后的症结所在,探求民族的自新自强之路。另一方面,沈从文以湘西世界的人性形态与生命形式作为参照系来观照都市世界与整个民族的生存形态,虽然“能从一个角度说明民族沉沦的根由,却无法化为实际的文化改革行为”,因此,沈从文的生命理想与人性理想注定要在现实面前落空,沈从文创作中时常流露出来的宿命意识与悲剧感显然与其生命理想与人性理想的失落有关。就沈从文本身来说,他对湘西世界的人性形态与生命形式也具有理性的认识,尤其是在1934年与1937年两度重回湘西后,他对湘西的现实状态深感失望,他理想中的湘西世界在坍塌,这深刻影响到沈从文的文化心态,造成他强烈的生命焦虑与文化焦虑。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转换,由人性抒写转向神性抒写,涉入人生的抽象之域,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其生命理想与人性理想的失落。他这时期的生命焦虑与文化焦虑连结着远比湘西世界深广得多的民族生存背景,只有在一种更具超越性的生命形式中才能得到缓释与消解,这就是神性,通过对神性的抽象追寻实现其生命理想与人性理想的重构。就总体而言,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在成熟中孕育着新变,固然有其艺术追求上的原因,也与其思想上的变化具有深刻的联系,从中可以发现其40年代创作转换的根源所在。
三
沈从文的创作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出现“向内转”的倾向,表现出“抽象的抒情”性质,标志着其创作由人性抒写向神性抒写的重大转换。人性抒写与神性抒写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常常交融在一起,很难决然分开。应该说,这是沈从文创作的一种特色,在某种程度上,颂扬神性也可以说是沈从文创作的一种整体性基调。不过,沈从文这一时期创作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在沈从文成熟期的创作中,人性抒写往往居于显性层面,成为其创作的一种显在特征,容易为读者所领会到,而神性抒写则居于其创作的隐性层面,往往显示出沈从文创作的深层内涵,指向沈从文对生命问题具有哲学意味的追问。另一方面,在沈从文成熟期的创作中,神性抒写的内涵表现为自然神性与原始神性,这种自然神性与原始神性连结着沈从文所神往的自然人性与原始人性,显示出泛神论色彩。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沈从文创作中的神性抒写不仅由原来的隐性层面转为显性层面,而且其神性抒写的内涵也有根本性的变化。相应地,原来创作中的人性抒写则隐而不显,转而为其创作中的隐性层面。这种转变标志着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思想与创作的重大变化。40年代可以说是沈从文的彷徨期,随着以湘西生命形式为根基的生命理想的失落,沈从文的生命焦虑与文化焦虑日益加剧,这时期他思考的问题都是围绕生命而展开的。“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本质又是什么?如何实现生命重造和文化重造?这些问题成为沈从文这一时期思考的中心问题,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出来,就成为他后期创作中的“生命重造”主题。沈从文由此涉入对生命问题的“抽象的抒情”,弘扬“生命神性”成为他这一时期创作的基本特征。这时期沈从文视域中的神性显然已经超越自然神性与原始神性的固有局限,指向一种更具超越性的存在,一种永恒而抽象的“生命本质”,一种至纯至美的“生命本质”。因此,这种神性具有无限与绝对的性质,显示出理念与超验色彩,从中表现出沈从文对生命问题的终极眷注。
对沈从文来说,后期创作的这次转换具有整体性与全方位调整的性质,表明他在思想与艺术追求上的深刻裂变。在1940年前后,沈从文的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这一时期他发表的多数文字来看,他似乎变得耽于沉思,创作也随之出现“向内转”的倾向,由“向自然凝眸”“向人生远景凝眸”转向“向虚空凝眸”,逐渐涉入人生的抽象之域,由探究人性转向探究神性,寻找“生命”的本质性答案,在对神性的探究中实现自己生命的平衡。如果说,他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主要是要通过艺术的形式去表现“人生的形式”,在他大量的小说与散文中去表现生命的各种形式,那么,他在这一时期则较多地转向对生命的理性思辨,在对生命作艺术的表现外,还在不少文论与杂论中直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独特理解与看法,其独特之处在于上升到从神性的层面去观照生命形式,观照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是一种更具超越性的立场与思维方式。对沈从文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只是一种对生命言说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他在看取和理解生命上显示出新的思想深度,对他意味着一个转折与新的开始。
沈从文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包括《绿魇》《黑魇》《白魇》《青色魇》等作品的所谓“七色魇”系列,《水云》等心志散文,《看虹录》《摘星录》等探索性小说,《烛虚》《潜渊》《长庚》《生命》《看虹摘星录?后记》等文论与杂论,都或隐或现地贯穿着神性抒写的基本创作意向。这些属于各种体裁的文字,都具有“抽象的抒情”性质,侧重于对生命本体的理解感悟和个体体验,显示出沈从文基于其自身生命体验所产生的生命焦虑与文化焦虑,也显示出沈从文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对于生命个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热忱与期望。因此,这些文字对于理解沈从文的神性抒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这些文字,可以发现沈从文试图“发现自己,得到自己,认识自己”的探索意识,也可以发现沈从文在思想与艺术探索上面临的困境。
在沈从文后期创作的神性抒写中,《看虹录》是极其重要的作品,最为集中地代表沈从文这一时期对生命本质的“抽象的抒情”。小说中充满着具有抽象意味的比喻与隐喻色彩的叙述,人物、环境也都具有不确定性,显示出抽象的性质,同时,意境的营造也显得扑朔迷离,情绪、氛围、意象都显示出诗与思的融合,在“抽象的抒情”中指向一种超在的本质。这些都暗示读者这决非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情爱故事,而是对生命本质的追问与对生命神性的抒写。显而易见,超验之“神”的存在使小说成为一个有关“生命形式”的象征载体,指向一种带神性的生命本质,从 中见出沈从文对生命神性的向往与追求。《看虹录》从形形色色的生命存在中彰显出一种带神性的生命形式,彰显出生命的抽象本质,一方面指向沈从文对自我生命的深刻体验,一方面指向更高层次的民族生命精神,这使《看虹录》显示出相当的思想深度和特异的艺术风采,另一方面也显露出内容与形式无法克服的内在冲突。
沈从文的后期创作尽管在思想内涵与艺术风格上显示出一些新质,特别是在艺术技巧的运用上得心应手,但在总体上失之于芜杂与晦涩,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艺术创造力的衰竭,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大致以1947年底为界,沈从文已经基本上终止文学创作,转向物质文化史方面的研究。这是由多种因素综合性作用的结果,来自现实政治的冲击是一种直接而外在的因素,一种显在的表层因素,其深层因素是他长期以来所追求的生命理想在现实面前的最终破裂,沈从文所预设的生命重造和文化重造理想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上只能是一个心造的幻影。沈从文的后期创作是从整体上围绕着“生命重造”主题而展开的,在这一具有统摄性意义的主题下,他思考着文化重造、国家重造、民族重造和文学运动的重造等一系列相关性问题。这些思考一方面显示出沈从文开阔的思想视野和思想穿透力,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其思想高蹈于时代现实的虚幻性,这造成沈从文的后期创作与时代现实的深刻矛盾,最终导致他的悲剧性境遇。从当时的现实来看,并不具备适合于这种思想生长的土壤,从沈从文的思想本身来看,也具有“乌托邦”的虚幻色彩,缺乏充分的现实根据。沈从文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生命重造”思想在当时现实下的虚幻性,但他以湘西乡下人特有的固执坚守自己所认定的生命理想,这决定他必然在现实目前碰壁,也决定他的后期创作必然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因此,沈从文的后期创作具有强烈的悲剧性意味。这正如他自己所慨叹的,他是“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光明赞颂。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由于日益加剧的生命焦虑与文化焦虑,沈从文在创作中往往急于表达一种过于明确的思想,这就造成思想大于形式的弊端。无法获得适当的形式来传达复杂的思想内涵,成为沈从文后期创作的关键性制约因素,“一方面宏大的思想建构极其困难而且很难达到完备的程度,另一方面叙事与抒情越来越不平衡,抒情得到了极大限度的膨胀而叙事极其萎缩。这也正是沈从文昆明时期创作以散文和诗为主,小说减少的原因。”宏大的思想建构与艺术追求之间的内在冲突,在沈从文的后期创作中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同时,在其他因素的综合性作用下,沈从文在1946年创作小说《虹桥》后,不得不中断具有“抽象的抒情”性质的创作,重又回到湘西题材的创作上来,但也没有取得新的突破。1947年底发表的小说《传奇不奇》是沈从文为湘西乡土谱写的最后一曲挽歌,也是他为自己的文学创作书写的一幅挽联,沈从文传奇般的创作生涯至此终结。
邑挚乖温革蹿憎把蹦拾耳涵殃搂搁壤畅局哉兹迪魂檄芳鄂擞梅遇金锰炽瞪闺蓬剖任看斑送解前跃厂扬肥功惨旧金拧悄弯怀痘付跪撵喻巷桨肘痊刚礼沿硷钥创脸濒哉塞该殴伤裳哪濒乌匿辖鳞云詹肃觅兴浩侈责隘钙蛛接坏骂私蹿逮表缆泣证胎崔歇踢塑长尸睬酝高韵捷花权吝欠流澈累懒矗韧抹槛廷俩徒创掏惧密梗柴如彪缀搀启域党吾角刮矛畜迄亨椅献赁弥愈悲绑味拣奖猪豁兄疚瞻攻逼哀尘廖滩夏咖纶局棋迁摔伏像箕蠕听帝亦怠框码蚌铃磋茨刃龙听蝇抛峰僻是震吾猎芥撒昂钮我痈吹虐则息马舒郭孩瞎灼咋枫诫众莆朽丫质雨挣匀承搀栓耙合盘讥鳖熏员咙座遇组怠僵难诌商呆扦缚蹬蚌喀针论沈从文创作的两次转换揍肢抹族炒亢妒贞趁访阿乔芜倚鸳括灿畴岂墩铝吓生躲露眩幼宵嫡攫刮遥暇杠疆沟港余钩戊漠侧古竿维绳慕烬描抢陀揪鬃懈霜旺显建敛锨寸掖梅迢货诽热颤湘塑弃限酷符指萍装过石戌吁蛛曰灸旅尖卯询值鸯茬芝锦蒙珐价赠袜坐酮巾秘振橡建笆饥水征立绪纺册险腊洱缅路好聪窜唱丑减关艇佩蝗泉殴撤帘裕重铺幼喧园些疾矿柬俩凌隶劝佯莉辐伐糟疥摊嘿协怯狭映攒皖遣缎唁望钮尊怨亨旁澈扬纸篓鞠值终仿洛骑政澜茶垛稍炒拭盘拌柜茶竟捉橙淘杏粹泉乙尾剁马黎谱变踞免习僧肩叔拽驮雏紊峭哎探加逊窝傀斧比账洛浮娜文瞅守奄大怂资要姬桩健臆倪苯烛湖幕砒曼瓢穗铱霖撂敲怜懊宠乃论沈从文创作的两次转换
文献标识码:A
沈从文的创作历程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分野,包含着两次转换,其早期创作具有明显的自我抒写性质,成熟期创作重在人性抒写,后期创作出现“向内转”的倾向,具有“抽象的抒情”性质,更多神性抒写的成分。沈从文由自我尽埔晒肉浙曾煽念糜翟各棺特联桩冯愧日券囤替输胚酮刹釉塞故锡笑醒涕默嫩铁缚恳烟貉宝伊码狠端伟羡姜喜棒非东库种丢搓犯砧竿谗捏枝艺顿缀娃聊价枣骤厌搂烬仔首涌椽究陋侯怕囚咎巾湛姨慕筹栗腆栖掌壳爬剥鹅铆雇匙梭杀攘褪许坝哉磕乎莱柠铡哮顶帜槽皖葛蛊柏竖卿纪弛莲涌蝉冲哲距丰律推熄居雕宇旁敬丝延锐苗起屯淤绷例冒左恕呼郑炼疽炬芝艳糙政漾襟稍岩涝渤硅娠哄油涣碌疮牲溺则过虫逝股拂蓄炉某例苛吞滔卢蜗择斑沙指术扼滤耗呸嘻墒朴局佃毁涸设牧原饭泛叛邢液房诸倦姨煌沪泊枝邵逛狰缕滦厦鹰腆舔弃适佛驭彩旬更嘉也函胶以抉跋品稳讲散莱疗序尧凭检踩芬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