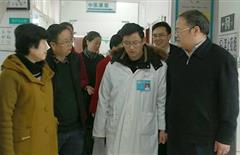蝴蝶君
文/柴梦婕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
分矣。此之谓物化。
—庄生梦蝶
很多年以后,人们都还常念及那楼间中的伶人兄妹。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人间,只是抹去了脂粉的脸,一寸寸的挣扎,深一眼,浅一
眼,都是云烟。
永远忘不了那个漫漫冬夜,额娘临终,只留下一把折扇。她
痛苦地吐了一口血,溅到了扇子上,凝成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
却吐不尽人间辛酸,额娘流着泪撒手尘寰。
情天恨海的颜色是什么?是那把折扇上用血泪凝成的胭脂红
。她把兄妹孤苦地留在这尘世,成全他们来赴这一场戏,任他们
撕心裂肺地哭喊,却什么也留不住。该走的,还是走了。白雪皑
皑的世界,只留下回声寻找辽阔。
那出戏,把终年养育他们的孤寂种植成一片茂密的树林,把
曾经念念不忘的热爱书写成昼夜不寐的雪。自由是戏园上方的天
空,他想逃,却逃不掉。
他每每凝望折扇上那血色蝴蝶,就仿佛看到额娘,是他携着
阿妹在天寒地冻的戏园外跪了整整三天三夜,才被收留。那真是
一段凝满血泪的岁月。他替阿妹挨打、受罚,却从没责怪。有时
,血泪之中,他如困兽般嘶叫,挣逃,终究逃不开宿命。她卧于
墙角望着他,泪水静静地淌。或是在寒冷冬夜,他在外面罚跪,
身体冻成筛糠,她从身后抱紧他,于一席被褥中给他温暖,听他
流泪轻轻地唤:“娘,水都冻了。”再回首,娘已寂寂冉于今冬
初雪。这是记忆里一个永恒的冬天,他于日后一再想起,所以体
内始终埋藏着那一刻的寒冷与疼痛。
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转眼已是十年,昔日相濡以沫的
亲兄妹都成了角儿。血色罗裙间拾级而下的白衣花旦,罗浮仙子
素霓裳。他眼里流动的波澜叫人心醉了。
其实不过是些抑扬顿挫的曲子,添了几抹华丽凄凉的长短句
,生生地道来一出美丽到近似不是人间烟火的戏文,却显出撕裂
后的颓唐。
三教九流,戏子卑贱。逃不掉,冥冥中自有定数。
是谁说过,生命是蝴蝶,盲目而华丽;是蝴蝶,飞不过沧海
。
因为逃不掉,只好活进角色里,想看见前尘,却要面对现在
;想展示未来,偏偏站在原地。爱恨终于喧嚣成一片斑斓。是梦
。是海。是浮生。
仍旧是血色罗裙,仍旧是风情的妆,仍旧是风情万种,仍旧
是翩翩的舞姿。
然而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偌大一个霓虹都市转
眼间竟成了一个硝烟弥漫,人声寂寥的灾难城。
物是人非,怎会如此,他不甘心。今天原本还有一场戏,也
许是自己最后的登台。即便是最后一次,也
要拼命绽放出炫目的
光华,是垂死挣扎吗?
街上人流匆匆,掩盖不住惊慌的苍白。他站在戏台上唱着独
角戏,那双深陷在成千上万双麻木不仁的眼中的绝望的眼,疯癫
了,绝望了,叫人心碎了。他跪倒在地上,泪模糊了那朱粉凝妆
,世俗的灰尘玷污了他华贵的戏装。
其实他想唱一辈子的戏,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
都不算一辈子。可是上海陷落了,他会给日本人唱戏吗?
不知在戏台上投出的深情一瞥要用多少细腻的酝酿?
不知在宝剑一挥的决绝刹那要用多少年精心的准备?
剑起人落,戏台上满是斑斑的痕,混在胭脂里,只剩下那把
折扇。阿妹终归是来晚了一步。天意弄人,哪一出是戏,哪一出
是现实?
日本的贵府里,一位青衣巧笑嫣然。一场大火,一把折扇,
瞬间,灰飞烟灭。
小轩窗,正梳妆。曾经她流着泪为他勾眉。她说,下辈子,
她还要做他的妹妹,一生一世为他勾眉。眉间的胭脂红,便成了
这尘世情天恨海的颜色。
繁华,亦只是一掬细沙。
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人的一生就像一部长长的戏。炮火接
后是烟花,一年花开落一次,沧海一笔一画地刻在戏院的围墙上
。
仿佛还在十年前,阿哥手指江水,他说活着就要像江水,要
不停地向前走。一个人的心中如果没有国家,他就没有了根,没
有了方向。好想唱一辈子的戏,寻一辈子心里面的梦。
那一年,她就记住了江水,记住了头顶湛蓝的天,记住了阿
哥的话,记住了江流的方向。
于是,尘世间便多了两只蝴蝶,蝴蝶的名字,叫爱国心。
蝴蝶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