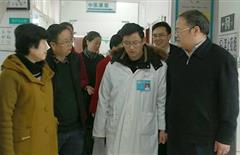见字如晤,那些写信的岁月
发布时间:2018-10-08 00:32:33
发布时间:2018-10-08 00:32:33
见字如晤,那些写信的岁月
见字如晤,那些写信的岁月
2014-10-09 11:07新华日报
10月9日世界邮政日
今天是世界邮政日,一个令人感怀的纪念日。如今,日新月异的通讯技术消除了时空距离,写信几乎成为行为艺术。而在从前,正是关山阻隔、鸿雁传书,令情思得以沉淀、绵延—阔大的时空才能孕育深邃的心灵。任何信息都能即刻抵达的时代,少了“见字如晤”,少了蕴藏于字里行间的情感传递,令人怀念那些写信的岁月。
家书抵万金
南京叶兆言
文革中,北京的祖父频频给父亲写信,总是不见回信,祖父很悲哀地对我堂哥说:“你叔叔怕是已经不在了!”祖父的朋友很多走了绝路,譬如老舍、傅雷,祖父自然会这样想。
父亲不回信的理由十分简单。他人在“牛棚”,所有信件,不管来去,必须先由“造反派”检查。父亲是个随和的人,偏偏这种事会顶真,觉得是人格污辱,一赌气,干脆不写信。父亲到了老年,体会到祖父当年的等待与忧虑,常为自己可笑的固执而内疚—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文革后期,我在祖父身边待了近一年,成了祖父的邮递员。那是一段很寂寞的日子,大家庭中,百分之八十的人流落在外—干校,农场,北大荒,陕北高原,写信成了祖父最大的安慰。天天盼信来,有信必回,写好立刻让我骑车扔到胡同口的邮筒里。我总是一次买许多邮票,害得营业员小姐起疑,不得不多看我几眼。
书信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言而喻。先说近。北伐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历任市长中,马超俊的任期最长。马夫人沈慧莲,曾经是广东农村的小学教师,闲时有个差事,为农妇代写书信。当地男人很多远赴南洋。有一位少妇,丈夫一去多年,少妇怀疑丈夫有外遇,请沈慧莲写信狠狠骂他一通。这显然是一位美丽的少妇,她的怨恨打动了待字闺中的沈慧莲,沈灵机一动,表面上全盘答应,实际上反其道而行之,把平时的文学修养,从唐诗宋词到古今中外小说,种种伎俩都施展出来,写了一封爱意绵绵的情书。少妇的丈夫被深深打动,立刻收拾行装,重返故里。
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代人写信是一种职业。一位朋友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一位替人写信的老先生,每次只收一角钱,去掉8分钱邮票,再赔上信纸信封,写一封信只赚一分钱。给我留下记忆的,是夫子庙邮局门口一个代人写信的老头。小时候,我们家的一个保姆住在秦淮河边,常常带着我溜回家看她的小女儿。每次从邮局门口走过,都能看见那老头,瘦瘦的,一头乱发,很寂寞—我从来没见过有人找他写信。
再说远。古人虽然普遍觉得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然而一些敏感之士意识到事情不会这么简单。譬如屈原《天问》就说出自己的怀疑:“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不知世界有多大,就说自己位于世界中心,显然站不住脚。中国人很容易自大,不过也有变通,有句老话“人挪活,树挪死”,就不把世界中心当回事,而是充满背井离乡的开拓精神。还有句老话“叶落归根”。这两句话合在一起,一去一来,书信做这中间的纽带,所以书信中有第一流的好文章,成为中国文学作品的一部分。
中国自古重视邮政,官方有驿传,民间有信局。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汤寿潜为交通总长。汤是旧官僚,不想干实事,只是看中总长这个头衔,不久便躲到上海的租界享清福,34岁的次长于右任成了交通部的一把手。于右任着手的第一件事,是发行中华民国光复纪念邮票,以新耳目(邮传本质上也属交通)。
新邮票尚未印出之前,大清邮票加盖“中华民国”字样,继续通行。曾任邮政总办的法国人帛黎,标榜邮政中立,在大清邮票上加盖“临时中立”字样,公开销售。于是同时有三种大清邮票流通,两种分别加盖“中华民国”、“临时中立”,最荒唐的是第三种,既加盖“中华民国”,又加盖“临时中立”,两行字垂直交叉。于右任觉得这是洋人有意分裂共和,有损中华民国国体,电令取消。
邮政是否发达,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业务量。早在晚清之际,南京成立官办邮局。开始租用的房子很小,月租金仅20元,民间信局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南京人也抱观望态度。后来发现,由邮局寄信,不仅按时到达,而且便宜,还不向收信人收取酒资—收取酒资是信局的陋习之一,官办邮局的地位就此确立。
民国初年,江苏邮务管理局花费25万大洋建了一幢三层大楼,后来在贡院街建了一个阔大的邮务支局。到20世纪30年代,南京已有邮局14所。
邮政的地位历朝历代都非同一般。邮政官员始终是肥缺,年轻人能吃上邮局饭,算是交了好运。南京的民国建筑中,铁道部和交通部的建筑均属一流。交通部大厦是以建筑“邮电部”大厦为名建成的,靠的是邮政专款。交通部大厦也就是现在的解放军政治学院,由建筑大家杨廷宝设计,1933年建成,墙外有护城河,楼前有花圃、园林、小桥流水,室内有暖气、地毯,座椅全系皮垫弹簧,有巨大的舞厅,悬挂着精致的壁画,四周有五彩壁灯和挂灯,气派犹如皇宫。
1937年出版的《中国交通之发展及其趋向》一书这样写道:“近数十年来,国营事业中,差强人意者,首推邮政。”
邮政有钱,政府挖邮政的钱就习以为常,用于战备,无限度地津贴中国航空公司。邮政是官僚资本,既沾官僚资本的光,又难免吃官僚资本的亏。邮政看家的挣钱手段,是“邮政储金”。据1935年的统计,全国邮政储金局700处,储户约20万,储金达5000余万元。抗战后,南京邮政再次迅猛发展,可惜当局理财还是不行,最后,邮政也快被拖垮了。
邮票与
“远东来信”
徐州张新科
爱好集邮,竟然因此开启了我的另外一番生活—整整18年,付出的心血凝聚成一部近40万字的小说《远东来信》,方寸邮票于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我小时候,父亲是县中校长,不时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出息学生的信件,为了争夺信封上那枚小小的邮票,我与几个姊妹闹得不可开交,父亲总会呵斥:“你们以为那只是个画片?!”是啊,邮票设计的匠心、精致的印刷值得品鉴,承载的历史、文化、审美和情感更令人回味。
年岁渐增,我开始拥有自己的信件,上面的邮票再没人和我争。留德期间,我喜欢旅行,每去一国一城,必定要去邮票店,遇到跳蚤市场,更是一头扎进去“淘宝”。十几年来,收集了上万张世界各地的邮票。
在海外,常常听人谈论二战,耳濡目染,我也开始留意有关中国与二战的历史。1995年,我在一家德文报纸上偶然读到二战期间中国上海收留犹太人的故事:1933年至1941年,为躲避纳粹的迫害,数以万计的犹太人逃亡海外,当时欧美各国慑于纳粹淫威而紧闭国门,正在被日寇铁蹄蹂躏的中国却无私地将他们拥入自己的怀抱,先后接纳了近三万名犹太难民,向他们提供庇护。但由于当时战乱频仍,大量历史资料遗失,加之巨大的语言障碍,还原事件困难重重,以至于很少有人了解这一史实的详情。我决定以小说的形式再现这段历史,因为比起学术论文、散文或者报告文学,小说更通俗,影响力更大,而且长篇小说能够承载历史的厚度与跨度。
从此,我18年如一日地收集整理德语、英语、汉语关于这一事件的档案、报道、画册等一手资料,为此去了法国、波兰、捷克、意大利、挪威、瑞典,购买了两百多本有关纳粹迫害犹太人的书籍,4次去上海舟山路当时的犹太“隔离区”参观,采访仍然健在的知情人。2012年寒假,终于开始写作小说。故事发生于上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的汉堡、上海、河南上蔡三地,如何将巨大的时空收纳在一部小说之中?多年来对邮票的收集和研究为小说的建构带来了灵感—将信件作为故事的线索和主要元素,设置“8封信”,带着读者在汉堡、奥斯维辛、上海、开封、上蔡、大西洋、太平洋之间跳跃,在30年代、40年代、90年代之间穿梭。
小说的信息量很大,所有细节既要严丝合缝,又要符合历史原貌。我于是遍访波兰集中营、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汉堡犹太人协会,6次观看柏林、波茨坦、纽伦堡、慕尼黑、德累斯顿、巴黎、诺曼底等二战场馆,收集了许多三四十年代波兰与德国之间、上海与德国之间犹太人的通信。一名犹太难民在给欧洲的舅舅信中这样写道:“我没有死,我活在上海!”一个名叫Jerry Moses的7岁犹太男孩历经生死,抵达上海后把那里视作“天堂”,他在给亲人的信中说:“我与中国孩子一起踢毽子,玩跳房子游戏,我童年的心灵始终留在上海,我充满感激的心永远留在中国并世代留存!”另一位犹太难民这样写道:“欢迎前来上海!从今往后,你们不再是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人、罗马尼亚人……在这里你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做犹太人!”
我不仅根据这些信件的内容构思故事,还对这些信件的样式进行“文本分析”—信封的式样、颜色,信封上地址的书写格式、习惯,邮票的款式、内容,邮戳的大小、形状,邮戳上文字、数字的字体、排列方式,等等。最终小说写就:德国汉堡的中国留学生谢东泓,在跳蚤市场上淘到8封旧信件,是犹太男孩雷奥于1938年至1945年期间,从中国写给他在德国的音乐老师的。谢东泓通过对这8封信的翻译整理,以及两次去上海、河南实地采访,揭开了深藏其间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史过往……
《远东来信》在《当代》发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封面设计成航空信封的样式。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等几十家媒体报道。德、美、以色列的出版社有意出版此书,中美制片人在商讨电影改编的事宜。但愿世界上有更多的人通过“远东来信”了解中国人的人道情怀和英勇无私。
小时候,父亲呵斥我们:你们以为邮票是画片?邮票的确不是画片!
高邮,
因邮而生
高邮陈永平
我在电视台当播音员时,给一部介绍本地风情的纪录片配音,片中有这样一句解说词:“高邮是全国唯一以"邮"命名的城市。”我有些纳闷儿,直到对自己生活的城市认识加深,才明白“邮”对高邮而言自有其丰富内涵。高邮因邮而生,因邮而兴,邮传、驿传与高邮的渊源非同寻常。
邮在秦代是通信系统的总称。秦王嬴政于公元前230年在洼地上筑高台、设邮亭,是为高邮。今天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属里下河地区,水路纵横,水网交错,秦时应该不是宜居之地;但因为邮亭的设置,迅速积聚了人气,才过了100多年,汉武帝便在这里设县,以后由路、军到府、州,又到县、县级市,绵延2000年,“那高邮州人生活在一个古今繁华的所在”(《醒世姻缘传》)。
高邮另有一个古怪的别称:盂城。该别称拜邑人秦观所赐:“吾乡如覆盂,地处扬楚脊;环以万顷湖,天粘四无壁。”盂即水盂,文房用具,用来贮砚水,多为扁圆形;秦观将故乡地貌形容为倒扣的水盂,很是贴切。明朝驿站正兴,高邮州一州两驿:秦淮驿和界首驿。乞丐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嫌前朝蒙元人少雅兴,命人给驿站改名,秦淮驿更名为盂城驿。我不知道秦淮驿、盂城驿孰俗孰雅,后者更具指向性是一定的—高邮应该是全国唯一以“盂”作别称的城市。
盂城驿建在高邮南门外,紧挨京杭大运河,属水陆两栖驿站,鼎盛时有厅房100多间,驿马65匹,船18艘,马夫、水夫200多名。“遥想幡旗飘日月,南船北马何喧喧”(邑人汪曾祺语)。
驿站被现代邮政取代是必然的。1913年高邮裁撤两驿,1985年,在隐居70年后,盂城驿被重新发现,震动海内。我国邮驿史长达3000多年,历代建立的驿站难以计数,大都湮没无闻,盂城驿成为我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驿站遗存。我第一次参观盂城驿,是协助央视拍摄纪录片《邮传万里》,在驿站内竟意外看到原属我家的一张大理石桌。桌圆形,支撑桌面的木材是“海绵木”,即红木,造型古朴,极具艺术品位。我家住县革委会的公房时,大理石桌作为房内家具归我们使用,我从5年级到高中毕业,全部家庭作业都是在这张桌上完成的。我们本可以廉价买下它,听说市里有新用途,父亲慷慨地让人搬走了,不曾想多年后在盂城驿与之邂逅。此后,我对盂城驿更有了一份亲近,一份记挂,这也是我个人与邮驿的缘分吧。
邮驿主要传递政府的公文、信件,邮政才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以我这个年纪,当然通过邮局给人寄过信,也收到过朋友的来信,但我已经很多年没再写信了。我恋爱时没给爱人写过信。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住得也近,写信矫情。恋爱中的人都是诗人,我忙着写诗去了。结婚后时常出差,人在旅途,写过一些家信,除了可以想见的表白,也报告自己的近况,所在地的见闻,琐琐碎碎,毫无文采,字迹也潦草得可以。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我所有的家信都被妻子叠过,整整齐齐的,与结婚证、毕业证等重要证件放在一起。我们先后搬过三次家,这些信一直跟着我们。那些激情澎湃的诗却被遗落、被淡忘了。
与我同时代的人,我们一起目睹了书信的式微。这再次让我想到了邮传和驿传。现在,邮亭、驿站都已历经辉煌,完成历史使命。逝者如斯,我们没有遗憾,欣然接受信息革命带来的便捷服务,但高邮人应该都还记得住信的本意:言论诚实,真心实意。这是邮传、驿传给这座城市造就的品格。
十八春:
致邮差的情书
南京鲁敏
从1987年到2005年这18年,我的生活都与邮局那黯淡多情的绿色紧密相关:前4年,在江苏省邮电学校读通信管理专业;后14年,在邮政局的各个有趣或不那么有趣的岗位辗转。
邮电学校位于南京城南,我那时十五六岁,失眠症却已根深叶茂、如影随形。无数个深夜,我眼睁睁地听着洒水车开上了夫子庙的文德桥,开过了长干巷,开过了考棚小学(这名字真够古雅的!),然后向三山街、白鹭洲方向去了……终于,天慢慢亮了,我与下铺一起出去跑步。学校在中华门附近,我们便冲着那灰白色、枯萎般的城门,一边跑,一边瞧着它在视野里上上下下,慢慢地近了、大了,心中有一种近乎悲凉却又骄傲的情绪……由于来自乡下、一无所长,不会唱不会跳,又因为爱吃馒头和肉圆,到后来还有点小胖,我相当羞怯、自卑,跟男生很少说话,说话时一定脸红。但我很怀念邮电学校那4年,怀念我那个班—通信管理8701,怀念我那个宿舍—505室。直到现在,我都在以一种可笑的方式怀念—设置各种密码,总用这组数字来排列组合。
在邮政局的14年,如果用最快的速度闪回,大致如下:
营业员—我是狗皮膏药似的“大替班”,从包裹、特快、储蓄、报刊发行、国际业务到汇款,所有柜台所有业务我都齐活儿,谁休息我顶谁的台子。因为粗心,我赔过两次钱:一次是国际长途台少收了100块押金,一次是汇款台晚上结账少了50块。
劳资员—在区局,一个二级单位,每个月我都要用各种系数反复测算,试图替下属六七个支局的四五百号人划分出三六九等的奖金额,算得不耐烦时,摔过区局长的门,好在我碰到的局长都很好。
团总支书记—装模作样地主持过团总支的晚会,把头发扎上去,俗气无比地穿上红毛衣,跟邮局的单身汉们跳南京流行的小拉舞。还组织烧烤,准备了好多好多鸡翅啊!但我其实不太喜欢这闹哄哄的工作。
外宣干事—与各级媒体记者打得火热。南京的小报特别多,我每年发稿量都在450篇以上,简直大跃进啊!经常有稿费,15块!25块!我拿个小本子记着,美不滋滋的!
行业报记者—担任《江苏邮电报》、《中国邮政报》的驻地记者。我喜欢五个“W”的新闻体,那种言简意赅的新闻八股腔,挺可爱!那阵子采访真猛,全局一百多个单位全跑遍了!南京到北京的T66/67次长途邮件押运班,我跟过4趟。后来,我写过一个短篇《在地图上》,跟这些采访有一点关系。
办公室秘书—替4任局长做过秘书,年中、年末的全局工作总结、职代会报告等是我的主打产品,同时擅长写各种场合的讲话稿。为了帮助自己“入戏”,每次动笔前,我总会假想我就是局长本人,有一种胸有河山、俯视全局的宏大眼光……
所有这些岗位中,与文学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这一幕—
大概是1993年,那时除了读书笔记还没写过什么,我在新街口邮局坐柜台,苏童来买邮票,慢吞吞地说,要一张《古人对弈图》。我立即认出了他,但我沉默、平淡,像一个疲倦的营业员那样,把邮票卖给他,同时心中一声长叹:这辈子,除了阅读,我难道还会和文学发生其他瓜葛吗?2010年10月,叶兆言、苏童、黄蓓佳等老师来替我的新书《此情无法投递》撑场子,我向苏童老师提起这一幕,他茫然、无邪地笑着,因为他一无所知。
工作之余,我还“学”点了“文学”—一下班就去南师大听夜课。上课的时间,要么是暮春,要么是深秋,似乎全南京的春华与秋色都集中到南师大了,其夜色之好,到了令人伤神的地步……我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古代汉语”,兴之所致,每晚逐篇背诵那些诘屈聱牙的先秦散文。傻乎乎的自学延续了四五年之久。快要毕业的那年冬天,通过邮校同学介绍,我认识了他,微胖,话不多。我们到山西路的军人俱乐部喝茶,到古林公园看梅花。很冷的冬天,接下来是同样寒冷的早春,我跟他每次见面都像是与冷嗖嗖的风儿约会。春季班开学后,我像很多女同学一样,也有男朋友在校门外等着接我回家。我喜欢这种平庸的画面,非常之安全。不到一年,我就决定结婚。在镇江路的一个小公寓里,我在每扇窗户上贴上大红“喜”字,楼下的人经过时仰起头就会看见。
从邮电学校到南京邮政局,对这18年,我充满复杂的感情。我对社会生活有了较为充分、体己的感受,我破灭了各种梦想,我失去了父亲,我生了孩子,我养成了“秘书般”的性格,我变得世故而冷静,但也非常不世故、不冷静地爱上了写小说,决心一去不返。
那不可复制的
“灵光”
南京俞香顺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在乡下中学读书,偶然读到赵爽的《一个邮政职工的一天》。1981年,新疆伊犁14岁女孩赵爽,在万国邮联举办的国际少年书信比赛中获得第一名,顿时成为青少年的文学偶像。我因此知道了“万国邮政联盟”和“世界邮政日”。
2011年,《中国新闻周刊》刊登《赵爽:绚烂之后》一文:这位万众瞩目的文学新星后来“泯然众人”,现在定居德国。80年代,文学是社会文化的“轴心”,书信是人际沟通的重要工具,赵爽的成名因缘际会。三十余年之后,赵爽归于平淡,文学处于边缘,书信也退出了日常。邮政业务不断拓展,书信投递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中国很早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邮政制度,“里耶秦简”就有关于秦代邮政的资料文献。古代官方的信使一般称为“驿使”,书信站点称为“驿站”。中国是一个书信极为发达的国度,关山阻越、交通不便,书信是联系亲人、朋友、情人的纽带;寄信人心驰神往,收信人伫立企盼,可谓“寄托遥深”。古人将书信看得和面谈一样重要,有“见信如晤”之类的说法。
家书是最常见、最朴实的书信,唐代张籍写过一首《秋思》,也是明白如话:“洛阳城里秋风起,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诗里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细节描写引发了无数后人的共鸣。上世纪90年代初,家书仍然维系着游子的思乡思亲之情,李春波的《一封家书》旋律简单,歌词如同拉家常,唱得街知巷闻、深入人心。文人之间的书信来往则是雅人深致。中国古代有不少“尺牍”汇编,如《小仓山房尺牍》、《秋水轩尺牍》,是研究文学史、心灵史的重要文献资料。我很喜欢文人之间的书信酬答,书架上有三种近现代学人的书信集:叶圣陶和俞平伯的《暮年上娱》、施蛰存和孙康宜的《从北山楼到潜学斋》、谷林致扬之水等人的《书简三叠》。近年来,国内出版了不少民国年间文人名士的书信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然而,我更心仪的是当时文人之间的切磋琢磨之乐,可惜,与书信的淡出同步,这种文人风流似也成了绝响。情人之间的书信具有私密性,外人或者后人很难见其原文;但当我们阅读宋词中那些缠绵悱恻的篇章时,往往会有很强的“在场感”、“代入感”,为之动容。晏殊和晏几道父子留下了很多关于书信的名句,如“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泪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
一封一封书信,通过邮政系统、邮递员,从这一双手传递到那一双手,带着情感的温度。梁实秋的《信》描述了书信往来的乐趣:“家人朋友之间聚散匆匆,暌违之后,有所见,有所闻,有所忆,有所感,不愿独秘,愿人分享,则乘兴奋笔,借通情愫。写信者并无所求,受信者但觉情谊翕如,趣味盎然,不禁色起神往。在这心情之下,朋友的信可作为宋元人的小简读,家书亦不妨当作社会新闻看。看信之乐,莫过于此。”
与即时通讯工具相比,书信究竟有哪些魅力?写信充满了“仪式感”,写信者庄静自持,“一笔一画总关情”、娓娓道来;字迹往往体现书写者的性情,读信的人见字如见其人,如同面谈能够捕捉对方的表情,所以古人有“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之说。书信的对象一般是唯一的,兼之又是手写,所以书信具有“不可复制性”;借用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的观点,书信具有特殊的“灵光”(aura),这就有别于电子信件、手机短信等等。另外,即时通信工具的信息具有“碎片化”特点,“言情”非其所长,写信则可以沉潜下来、倾诉衷肠。此外,书信和纸质书一样,可以摩挲把玩、反复展读。不过,我想书信最大的魅力还是在于寄信、收信过程中,盼望、猜测、焦急等等复杂情绪的交织,用一个笼而统之的词语,这个过程充满“诗意”。
无论如何,书信已经式微了。我也不是“尸骸的迷恋者”,平时通信主要是电子邮件。不过我认为,电子邮件可以汲取书信的一些长处。比如中国传统社会重伦理,书信的抬头、落款很是讲究。然而,我收到的学生电子邮件往往既无抬头、又无落款。我有点文字小洁癖,在邮件的“主题”栏里总是写上自己的名字或是事项,从不马虎;而收到的信件,却总是在我的名字或事项前加个“Re:”,甚至好几个,让人气闷。我与台湾学人互通电邮,对方的礼数真是令人汗颜,抬头都是采用传统书信的“尊鉴”、“钧启”等等。另外,我们何妨偶尔体验一下执笔写信的乐趣呢?我所在的学院有一个延续多年的项目“一封家书”:每年中秋,让新生给父母手写一封家书,家长事先并不知情。家长、学生的反馈都不错。朋友、恋人之间,何妨偶一为之,领略那小小的惊喜呢?
曾几何时,“纸短情长”的书信如同梭子,织就了温情脉脉的人际网络;而严密的邮政系统为此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书信的形式过时了,书信的传情之“魂”永不过时。我坚信邮政不是冷冰冰的技术系统,会与时俱进,探索出新的人与人的沟通方式,让书信之“魂”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