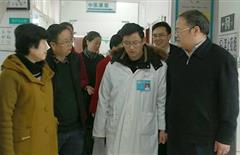名家托物言志文章
发布时间:2018-12-04 20:20:47
发布时间:2018-12-04 20:20:47
扛椽树
刘成章
这柳,这陕北的柳,这迎着漠风的柳,这晕染出一片苍凉的柳,千万年来,是在等谁呢?谁能描绘出他的满身奇崛?
滔滔黄河。滔滔的神话和历史。滔滔的云中飘带和地上脚步。自西周至春秋,花开花落五百年,星移斗转五个世纪,等来了古神州的第一批诗人。诗人们如鸟如蝉如蛙,吟诵之声不绝不绝。吟出了“风”,吟出了“雅”,吟出了“颂”,吟出了一部诗经,吟出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绝妙佳句。不过,此句绝妙是绝妙了——引得后辈子孙竞相模仿,竞相依依——但,它却与这柳无干。依依者在水一方,若窈窕淑女,不在陕北。陕北是满眼的干山疙瘩,依依者不是这柳。也难怪,这柳只生长在遥远的绝域,诗人们何得一见?
及唐,诗界的天空今非昔比,星汉灿烂。一颗星终于飘然而至,照亮了陕北。那就是王维。王维走马沙原,沙原边峙立着一棵棵杨柳树,因而,他一定看到它了。王维诗兴大发,脑海中如有巨鲸游动,咕嘟嘟冒出两个字:直,圆。柳啊柳啊,你这下总算等来了——人们说——凭着这直这圆,凭着这两种飞动的线条,天底下的什么物象不可描绘出来?但可惜,王维并没有让这线条继续飞动,而是让它蓦地凝固了,凝固为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这能怨王维吗?王维只在陕北呆了极为短暂的日子,他的诗思怎么会不首先激荡于阔大的风光?怎么能要求诗人把所到之处的一切都付诸笔墨呢?
一次一次地被冷落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碰到谁的头上,都无疑是重大的打击,都会有情绪上的波动。这柳,我心想它一定是一副失望的颓唐的样子了。殊料,它心静如水,仿佛世界上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翻开大地的档案,更知它千万年来,一直静静地观望,不曾激动过一次。
然而,当我的身影出现在柳的眼帘中的时候,柳不平静了,柳借漠风狂舞,首如飞蓬。而我,也恍若又见故人,顿生亲切感,真想喊着叫着猛扑过去。我感到了心和心的相撞,但我茫然不知何以如此。突然间,一个声音响在耳畔,唤我的乳名。我望柳,柳无言。望柳的枝头,一只乌鸦在叫:“章娃!章娃!”枝头上还有些鸟雀,它们叽叽喳喳,隐约在说:“等的是你!等的是你!”我欲问乌鸦,欲问鸟雀:“谁在等我?谁?”但不待我开口,它们已四散飞去,而就在这时候,阳光下,柳的影子已拥抱着我,如亲人温热的襟怀。原来,是柳在等我。哦,柳!陕北的柳!朴拙如庄户人的柳!令人兴奋令人落泪的柳!不等吟出《诗经》的诗人,不等王维,就等我!我诚惶诚恐:“我有什么能耐?为什么等我?”柳仍无言,柳让山上的放羊娃传达它的心声,歌曰:“陕北生来陕北长,因为你魂牵这地方。南瓜蔓子白菜根,不等你的才华单等你的心。”我怎么能不被深深感动呢?我该怎么抒抒情怀?我虽然也写过诗,却事实证明并没有写诗的灵气,我只有求助于李白了:太平洋水深万丈,不及此柳等我情!况且,我本来对它也怀着难分难解的情结。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描绘它,没有借鉴可寻。不论是关于柳的任何文字,都与它挂不上边。所以,什么峨嵋呀发丝呀的种种女儿气,应该首先在天地间扫荡净尽。不能有西施的影子,不能有林黛玉的影子,不能有刘三姐的影子,甚至京华柳的那种绿,江南柳的那种绿,灞桥中原柳的那种绿,在这里也可以忽略不计——只用黑,黑还要浓黑。于是,我把我周身的血液变成浓浓的墨汁,满腔满腔地往出泼。泼一柱疙疙瘩瘩的铁的桩子,泼一片铁的定格了的爆炸,泼一股爆炸了的力的冲击,或者泼成曾经跃起在这儿的英雄——泼成蒙恬,泼成赫连勃勃,泼成李自成,泼成刘志丹和谢子长,也可以泼成这儿的无数死了的或者活着的普通刚强汉子。我还想把它泼成鲁迅,鲁迅虽是南方人,但他的骨头却像这柳,我要泼出的是鲁迅的黑白木刻般的雄姿。——这就是这柳。
倘问:这柳没有枝条吗?有。但它的枝条不是垂下来的,而是横在天空中的,像爆炸射出的众多而凌厉的轨迹,像英雄举起的密密麻麻的刀枪。它的枝条是陶渊明的腰,五斗米也压不弯它;它的枝条是鲁迅的笔,其笔如椽,挥尽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辉煌。
说到椽,这柳的枝条,确实是做椽用的。人们砍了它用来盖房子。一棵树可以砍六七十根。但砍了它,用不了几年的工夫,又一层新的椽子又蓬蓬勃勃地生成了。生了砍,砍了生,往复无穷。往复无穷的是瘠薄的土地上的悲壮的奉献。它常常悲壮得像断肢折臂的战士,即使年迈了,衰老了,躯体变得瘪而空洞,甚而至于剥落成扭曲的片状,仍不忘耗尽最后一丝骨血,奉献于世界。如果把它一生的奉献累加起来,每棵树都应该是一片森林。——这就是陕北的柳。
我的描绘如果就此结束,我知道,还是对不住它的。我还应该用我满腔的浓浓的墨汁,泼出它的名字。有人把它叫做塞上柳,有人把它叫做蓬头柳,有人把它叫做扛椽树。我特别喜欢最后这个名字,因为它摒弃了柔弱的柳字,更因为它以浓郁的泥土气息,道出了他的根本特质。那么,就让我在浓浓的墨汁中饱蘸上深厚的感情,像豪雨一样,通畅地泼下它吧——扛椽树!
泼下它的时候,应该再次泼下它的奇崛形象,那形象仿佛是黑桩子,黑碑石,黑煤垛,黑旋风,黑爆炸,黑白故事片中的黑脸黑衣“传奇英雄”,黑得使人过目难忘。这还不够,还应该泼出它黑色躯体中的代代相袭的“遗传基因”,以及由于这基因才一辈辈、一年年、永不歇息地“扛着椽”,扛着椽站起啊站起,献给父老兄弟姐妹,修筑广厦千万间。还应该泼出它的声音,那是负重的声音,那是拼争的声音,那是乐此不疲、坚韧不拔、不屈不挠、从来不说一个不字的声音,那是粗重的从胸膛发出来的喘气的声音。那声音如一股一股的大西北风,撼动北国大野!
4、蒲公英
壶井荣
“提灯笼,掌灯笼,聘姑娘,扛箱笼……”
村里的孩子们一面唱,一面摘下蒲公英,深深吸足了气,“甫”的一声把茸毛吹去。
“提灯笼,掌灯笼,聘姑娘,扛箱笼,甫!”
蒲公英的茸毛像蚂蚁国的小不点儿的降落伞,在使劲吹的一阵人工暴风里,悬空飘舞一阵子,就四下里飞散开,不见了。在春光弥漫的草原上,孩子们找寻成了茸毛的蒲公英,争先恐后地赛跑着。我回忆到自己跟着小伴们在草原上来回奔跑的儿时,也给小儿子吹个茸毛给他瞧瞧:
“提灯笼,掌灯笼,聘姑娘,扛箱笼,甫!”
小儿子高兴了,从院里的蒲公英上摘下所有的茸毛来,小嘴里鼓足气吹去。茸毛像鸡虱一般飞舞着,四散在狭小的院子里,有的越过篱笆飞往邻院。
一旦扎下根,不怕遭践踏被蹂躏,还是一回又一回地爬起来,开出小小花朵来的蒲公英!
我爱它这忍耐的坚强和朴素的纯美,曾经移植了一棵在院里,如今已经八年了。虽然爱它而移植来的,可是动机并不是为风雅或好玩。在战争激烈的时候,我们不是曾经来回走在田野里寻觅野草来吗?那是多么悲惨的时代!一向只当做应时野菜来欣赏的鸡筋菜、芹菜,都不能算野菜,变成美味了。
我们乱切一些现在连名儿都记不起来的野草,掺在一起煮成吃得碗都懒得端的稀粥来,有几次吃的就是蒲公英。据新闻杂志的报道,把蒲公英在开水里烫过,去了苦味就好吃的,我们如法炮制过一次,却再没有勇气去打来吃了。就在这一次把蒲公英找来当菜的时候,我偶然忆起儿时唱的那首童谣,就种了一棵在院子里。
蒲公英当初是不大愿意被迁移的,它紧紧趴住了根旁的土地,因此好像受了很大的伤害,一定让人以为它枯死;可是过了一个时期,又眼看着有了生气,过了二年居然开出美丽的花来了。原以为蒲公英是始终趴在地上的,没想到移到土壤松软的菜园之后,完全像蔬菜一样,绿油油的嫩叶冲天直上,真是意想不到的。蒲公英只为长在路旁,被践踏,被蹂躏,所以才变成了像趴在地上似的姿势的吗?
从那以后,我家院子里蒲公英的一族就年复一年地繁殖起来。
“府上真新鲜,把蒲公英种在院子里啦。”
街坊的一位太太来看蒲公英时这样笑我们。其实,我并不是有心栽蒲公英的,只不过任它繁殖罢了。我那个儿子来我家,也和蒲公英一样的偶然。这个刚满周岁的男孩子,比蒲公英迟一年来到我家的。
男孩子像紧紧扒住扎根的土地、不肯让人拔的蒲公英一样,初来时万分沮丧,没有一点精神。这个“蒲公英儿子”被夺去了抚养他的大地。战争从这个刚一周岁的孩子身上夺去了父母。我要对这战争留给我家的两个礼物,喊出无声的呼唤:
“须知你们是从被践踏、被蹂躏里,勇敢地生活下来的。今后再遭践踏,再遭蹂躏,还得勇敢地生活下去,却不要再尝那已经尝过的苦难吧!”
我怀着这种情感,和我那小儿子吹着蒲公英的茸毛:
“提灯笼,掌灯笼,聘姑娘,扛箱笼……”。
【赏析】
壶井荣(1900~1967),是一位日本女作家,她的《蒲公英》用优美、清新、细腻、抒情的笔调,表达了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重大主题。
我们可以多角度来解读《蒲公英》所具有的关。《蒲公英》看上去是随手写成的,一个战后被作家收养的孤儿和院子里随处生长的蒲公英,这是两个距离遥远的事物,可是他们内在的世界却是可以互通的,蒲公英强韧的生和小儿子失去双亲的凄苦的活,是那么相似。壶井荣说:我要对这战争留给我家的两个礼物,喊出无声的呼唤……蒲公英、小儿子、战争悲惨的历史,这三者自然地融合起来,使《蒲公英》成为在时间面前不会感到羞愧的文字。
本文构思巧妙,把三个片段集中地组织在一个场面之中,并用表现儿童情趣和反映生活的童谣贯穿首尾;写蒲公英和写那个小儿子,结合得非常贴切。本文运用了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以尺水见波澜,反映了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思考,对和平生活的渴望。
5、桃花心木
林清玄
乡下老家屋旁,有一块非常大的空地,租给人家种桃花心木的树苗。
桃花心木是一种特别的树,树形优美,高大而笔直,从前老爱林场种了许多,已长成丈高的 一片树林。所以当我看到桃花心木仅及膝盖的树苗,有点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种桃花心木苗的是一个个子很高的人,他弯腰种树的时候,感觉就像插秧一样。
树苗种下以后,他常来浇水,奇怪的是,他来的并没有规律,有时隔三天,有时隔五天,有进十几天才来一次;浇水的量也不一定,有时浇得多,有时浇得少。
我住在乡下时,天天都会在桃花心木苗旁的小路上散步,种树苗的人偶尔会来家里喝茶。他有时早上来,有时下午来,时间也不一定。
我越来越感到奇怪。
更奇怪的是,桃花心木苗有时(1)( )地枯萎了。所以,他来的时候总会带几株树苗来补种。
我起先以为他太懒,有时隔那么久才给树浇水。
但是,懒人怎么知道有几棵会枯萎呢?
后来我以为他太忙,才会做什么事都不按规律。但是忙人怎么可能做事从从容容?
我忍不住问他,到底应该什么时间来?多久浇一次水?桃花心木为什么(2)( )会枯萎?如果你每天来浇水,桃花心木该不会枯萎吧?
种树的人笑了,他说:“种树不是种菜或种稻子,种树是百年的基业,不像青菜几个星期就可以收成。所以,树木自己要学会在土地里找水源。我浇水只是模仿老天下雨,老天下雨是算不准的,它几天下一次?上午或下午?一次下多少?如果无法在这种不确定中汲水生长,树苗自然就枯萎了。但是,在不确定中找到水源、拼命扎根的树,长成百年的大树就不成问题了。”
种树人(3)( )地说:“如果我每天都来浇水,每天定时浇一定的量,树苗就会养成依赖的心,根就会浮在地表上,无法深入地下,一旦我停止浇水,树苗会枯萎得更多。幸而存活的树苗,遇到狂风暴雨,也会一吹就倒。”
他的一番话,使我非常感动。不只是树,人也是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4)( )的心。在不确定中,深化了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感知,就能学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生长。
现在,窗前的桃花心木苗已经长得与屋顶一般高,是那么优雅自在,显示出勃勃生机。
种树人不再来了,桃花心木也不会枯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