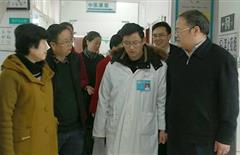论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局限
发布时间:2011-08-29 10:24:45
发布时间:2011-08-29 10:24:45
论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局限
——《红楼梦》与《安娜卡列尼娜》对比研究
摘要:《红楼梦》与《安娜·卡列尼娜》是两部著名的经典长篇小说,并且都以描写女性的命运为重要内容。通过这两部小说,研究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发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具有重要意义。《红楼梦》中林黛玉为代表的女性,在爱情和生活中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灵魂的自由。《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对自己的爱情执着追求,体现了贵族妇女个性解放的要求,具有反封建性质。虽然,她们都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对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探索具有同样深刻的意义。本文从女性意识觉醒的角度,对《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进行比较分析。两部书中的女性都走了一条反抗旧的、腐朽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争取理想、爱情和个性解放的道路。她们大胆的追求爱情与人格的独立,反对封建势力下对女性的禁锢同样执着、热烈。文章从黛玉的恋爱与奴婢的反抗中,我们看到了与传统女性迥异的独立自主的人格的凸显,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还只是一种朦胧的追求,但毕竟代表了一种新的观点,她们争求着平等,渴望着自由。而安娜不仅艳丽迷人,雍容优雅,而且表里和谐,还以其精神的美而具有魅力。她真挚、单纯、自然、善良,同时又有旺盛的生命力,炽热的感情和一个“复杂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在卡列宁那儿安娜得到的只是形式上的虚无的婚姻。安娜生活在不幸的婚姻中,她追求新的爱情,正是要求平等的一种追求。平等意识的觉醒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女性的解放首先应从精神层面上展开,只有当一个女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的时候,识到自己与男性一样应该而且可以平等地分享这个世界的时候,才有可能建立一种新的两性伦理关系,女性解放才有可能。
关键词:女性意识;平等;自由
《红楼梦》与《安娜卡列尼娜》是中外两部伟大的著作,书中的女性为争取女性的独立与自由都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书中的女性同样在爱情的呼唤下,经历自我意识的复苏、要求平等和抵抗社会禁锢的过程。她们强烈女性意识的追求,试从以下几方面探究。
“人”的意识的复苏
千百年来,在男性的主体意识不断强化,物的生产与精神不断发展的同时,女性在事人的家务劳动与角色定位中不断弱化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她们按照男性中心文化的女性观塑造自己,成为被物化的人,同时封闭的生活与愚化的教育更使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泯灭。但是,随着城市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阶级正慢慢地生发出现代的性爱意识,慢慢地体会着朦胧的个性觉醒,这一切都召唤着女性“人”的意识的复苏。林黛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的一个女性形象。在这个“眼空蓄泪泪空垂”的女性柔弱的外表下,蕴藏着别样的刚强。她努力摆脱着传统女性的奴性意识,她认真听从自己情感与心灵的呼唤,她大胆地触犯礼教的清规戒律。从林黛玉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生命意识的浮动。
黛玉用自己的生命和眼泪深爱宝玉,她与宝玉的爱情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经历过青梅竹马的了解之后产生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恋情。她一次次的试探宝玉,她所要的是宝玉眼中只有一个她。在当时社会宦官之家的贾府,宝玉就是有个三妻四妾也是很正常的事。然而,作为恋人的她——黛玉要求作为一个平等的人,与宝玉站在一起。虽然,黛玉对宝玉的痴情无以复加,但是并不使她丧失作为女性的独立与尊严。女性不应当是男人的花瓶与玩偶,也不是花几千两银子买来供玩乐的物品。她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是一个在爱情路上与男人平起平坐的人。对于爱情从不是谁对谁的施舍和盲从。书中写到宝玉挨打后托丫鬟给黛玉送去半旧的手帕,黛玉眼中浸满了眼泪,连夜在手帕上题诗。这种默契与相知是有牢固的思想基础的。所以,宝玉常常赞扬林妹妹从不说那些混帐话。林黛玉在叛逆封建主义的生活道路上与宝玉相知相恋,然而,当时的社会人情是不可能允许自由选择的,因此,当她的人生旅途在偏离常轨之后,她被迫面对社会安排给女性的严峻现实,那就是不许恋爱,听从家长的命运的安排,屈辱地生活下去。黛玉不愿意这样活着,她只有泪枯而亡。眼泪流尽的黛玉,为自己理想殉葬了,然而,她的死却是一个反抗者的死,一个觉醒者的死!
如果说黛玉的恋爱和反抗是在从行动上有了自我意识诠释的话,那么她的诗歌《五美吟》就是在思想上为女性意识做了更好注解。《五美吟》吟咏了历史上5 个著名女性的悲剧性命运:西施、昭君、绿珠、虞姬、红拂。在宗法制度下,这5 个女性都命运多舛,结局凄惨。她们的故事被文人墨客吟咏了无数遍。不同的是,在黛玉眼中,西施、昭君、绿珠都是被男权中心主义文化彻底物化、工具化的人物。林黛玉认为,西施与昭君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不光彩的筹码,一个以身伺虎,实施美人计;一个和亲匈奴,背景离乡。绿珠更是一个女性主体精神彻底消弥的形象,她临危以死报石崇,明珠暗投。黛玉以女性视觉直面这些女性的惨淡人生,对这3 个人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和惋惜。尽管黛玉还不可能直接批判男权政治以女性为工具的肮脏,但结合她对西施命运的惋叹,我们可知她对此是有所触及的。从她吟咏西施和昭君的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黛玉心中那正在成长的女性生命意识,她不象历代轻浮文人那样,从男性的角度,无视西施心中痛苦与挣扎,对西施充满艳羡,如王维曾不无羡慕地谈起她“朝为越溪女,暮为吴宫妃”,郑獬充满赞扬地说“若论破吴第一功,黄金只合铸西施”。她对这些最终不得善终的女性的同情,表现了她对女性生命本身的尊重与关怀。这种正在觉醒的人道情怀在中国的伦理生活中已经被埋葬了几千年。反观虞姬与红拂,林黛玉认为,她们是能够冲决环境,积极寻求自身的解放,从而走向自由之路的女性形象。这两人出身底层,但却看到了自我的人格与人生价值,并主动积极地进行人生道路的选择。她们不再是以色事人,不再是无条件地充当贤内助、锁在闺门之内,而是要与她们的爱人并驾齐驱,共举大业。因此,她们对传统文化是有所反驳的。诗以言志,言为心声,安知这不是黛玉的理想? 可笑苏轼对项羽“艰难独与虞姬共”的指斥,把虞姬视为祸水红颜,更可笑何溥“八千弟子同归汉,不负君恩是楚腰”的赞歌,把虞姬视为节妇。虞姬是祸水吗? 是为报君恩而死吗? 在黛玉的诗思里,虞姬其实只为自己的理想和操守而死,就象黛玉最终死于自己倾心相与的爱情一样。在专制主义权力与封建主义道德相互勾结,对女性全面而严酷地征服,占有,奴化的时代,黛玉的觉醒是非常可贵的。她通过对5 个女性的命运的叹息,表现了自己对不平等的两性伦理观的否定。她并没有象以往的文学家那样,站在男性政治和封建宗法伦理的立场去轻轻松松地议论这些悲剧,而是直接关注女性命运与情感本身,不袭前人地批判了男权政治这只污染了女人、污染了文学与历史的肮脏的手。尽管那些进步的文学家对这些女子的命运也抱有同情,对于男性也有批判,他们的立足点是站在宗法制上,因而他们的批判也只能是对某个人的某些品质的批判,所以,他们才在批判元帝的昏庸时,教昭君“莫怨东风当自嗟”,这样沉重的悲剧就让命运和偶然性一笔勾消了。
《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主体意识的形成是在伏伦斯基的介入后实现的。安娜自从遇到了伏伦斯基后,便陷入了一见钟情的爱。她神经紧绷着,手指和脚趾都在紧张地颤抖。她发现周围的一切是如此陌生:“那在扶手椅上的是什么,是皮大衣还是野兽? 我怎么在这儿呀? 是我自己还是别的女人?”在镜子中,熟悉的一切变得如此陌生,她初次认识了她的女性自我。伏伦斯基对她的爱后来证明绝对不是逢场作戏:“我们要是没有这种爱情,就说不上什么幸福和不幸福,而是根本就不能活下去。⋯⋯我和她都抛弃一切,两个人一起躲到什么地方去,除了我们的爱情,什么也不要。”安娜在他的感情中认识了自己的感情,她开始审视自己的婚姻:“八年来他怎样摧残我的生命,摧残我身上一切像活人之处,他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活的女人,是需要爱情的。”她审视她的丈夫:“他什么也不懂,什么感情也没有。⋯⋯他不是一个男子,不是人,是木偶! ⋯⋯他不是人,是一架官场的机器。他不懂得, 我是他的妻子, 他是外人, 他是多余的人。”她的女性意识慢慢形成:“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一个活人,我没有罪,上帝生就我这样一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安娜在爱情中展露了她的活力、智慧、情感、兴趣,在爱情中充实了自我。他们彼此在对方身上寻找自我,他们学会体验高尚的情感,感受由两人共同创造的生活,体验爱情带给他们的幸福和甜蜜。他们共同付出“关心、责任、尊重和了解”,这在弗罗姆看来,是成熟的爱必备的要素。他们“在互相认可中,每个人都在另一个人身上认出了自己,把另一个人当成另一个自己,另一个人也这样看待他。⋯⋯两个人能够迷失在彼此中但又不丧失自我。”在他们的爱情中蕴涵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尽管当时没有人认识到这点。这些在安娜枯燥单调的婚姻生活中是不曾有过的,也是伏伦斯基在花天酒地的军旅生活中无从体验的。卡列宁对安娜来说是一堵墙,囚禁她的热情,缩小她的生命价值;伏伦斯基对她来说是一面镜子,从他那里,她感受了自我存在,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安娜之所以爱上伏伦斯基,是因为他了解自己,觉得和他在一起能扩大自己的人生经验,实现她人生的各种可能性。
反抗女性、追求平等
处于封建社会的女性,受到“三从四德”思想根深蒂固的压迫。“三从”就是培养女性更好的为男性服务,强大的社会法则约束女性,只有听话才可以生存。在当时反抗奴性,追求平等成了女性的呼唤。当女性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生命有尊严的人的时候,哪怕这还只是她心中一种朦胧的幻想,也足以让她反思她所处的不平等的伦理关系,让她不可能再继续屈服于、匍匐于宗法等级制度之下了。反抗奴性、追求平等就必然成为这些女性生命中一道绚烂的风景。在大观园里,反抗的林黛玉并不是孤身奋战。从那一时代最受限制的社会最底层,已经依稀可闻被压迫者们觉醒的声音了。可以列举一大串这样的名字,她们和现实环境对立,充满反抗精神,要求个性解放。睛雯,司棋,龄官,芳官,尤三姐…… 等等。睛雯是平民丫头,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阶级地位赋予她一个极其光辉的品质,就是反奴性。她尽管身居奴才地位, 却认为“谁也不比谁高贵些”,她与宝玉在形式上是奴才与主子的关系,但实质上却是一种真诚相待、相互尊重的朋友关系。她从不认为自己是可以被主子任意歧视、侮辱、践踏的奴才,也鄙薄袭人出卖自己诌媚主子的卑劣品性。她天真、坦率、身为奴隶却无奴相气、无奴性,因此,她不见容于礼教,不见容于王夫人便是必然的事了。曲折幽怨深情美丽的龄官和芳官一样是贾府买来的小优伶,她们实质上只是贾府的家庭娱乐品,是被人视为三四等奴才甚至倡妇粉头之流的形象。但是,她们俩人却富于情感而强于反抗。龄官划蔷的深情痴意曾令宝玉为之发呆,而更出人意外的是她的自尊,多少人对宝玉娇宠有加,趋迎奉承,而龄官却对之冷冷淡淡,宝玉央她唱一套“袅睛丝”,她可以正词拒绝。她不也是一个没有奴性的奴隶吗? 她尖锐的敏感,沉痛的呼声,强烈的抗议又可见其不可侮的自尊与她对情感自由的渴望。书中描绘这些女优的生活,她们深刻的恼恨,真挚的友情,哀哀无告的痛苦表明她们很多人已经不是在既定秩序中自我奴化的麻木者,而是痛苦的觉醒了的新女性形象。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小丫头们也在为着自己的人格和基本权利在做斗争,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尤三姐、司棋、鸳鸯等人。她们都在暗暗反抗封建伦理道德这种命定的力量,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冲决传统的思想因素正在成长。鸳鸯自知象她这种“家生”奴隶,决计逃不出受人奴役供人淫乱的命运,因此,为了抗拒贾赦的逼婚,贾母命终后,她以死来保持了自己纯洁刚正的灵魂,做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些女奴们的反抗显然不是因为衣食无着而铤而走险,因为贾府对奴隶的基本态度是奴役加保护的,一方面把奴隶看作猫儿狗儿,另一方而却也给她们衣食温饱,还按月发钱, “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因此,奴婢们之所以反抗显然不是为了物质上的匮乏,而是为了争取“人”的尊严。她们已朦胧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主之权,意识到自己是“人”而不是会说话的工具,不是供人观赏的花鸟虫鱼,她们渴望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渴望被平等相待。而这种崭新的意识与愿望却和封建宗法制度所维护的等级秩序与世态人情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她们才遭到毁灭的命运。因此,她们是“以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价值而搏斗。”从黛玉的恋爱与奴婢的反抗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与传统女性迥异的独立自主的人格的凸显,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还只是一种朦胧的追求,但毕竟代表了一种新的观点,她们争求着平等,渴望着自由。平等意识的觉醒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女性的解放首先应从精神层面上展开,只有当一个女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的时候,识到自己与男性一样应该而且可以平等地分享这个世界的时候,才有可能建立一种新的两性伦理关系,女性解放才有可能。
安娜起初以卡列宁的妻子的身份出现在她所属的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但婚姻对安娜来说并不是出于自愿的,他们两人的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晶,更谈不上平等的爱情,这样的婚姻就潜伏着不稳定因素。安娜那貌似平静安逸的心里像火山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激情,毕竟安娜是一个年轻鲜活的女人。在和渥伦斯基邂逅之后,她那沉睡的爱的激情和生命意识被唤醒了。安娜开始懂得什么是爱情,她身上活生生的女人突然苏醒了,她发出了强烈的心声“时候到了”“ 我要爱情,我要生活”。此后,她身上流露出一种纯真的、发自内心的对真正生活的热切向往之情。在作品中把安娜和卡列宁婚姻的真正不幸归结为两人精神志趣的巨大差异。卡列宁把安娜仅仅当女人,而不是一个知心爱人,卡列宁从来也不知道安娜是一个和自己平等的人,他们在婚姻当中应享受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卡列宁是一个伪善、僵化、缺少生命活力的贵族官僚的形象,小说通过这一形象严厉批判了那个腐朽的沙皇封建制度和上流社会刻板、虚伪的道德规范。卡列宁平常严格地按照既定的社会规范生活。他遵守法规,忠于职守,作风严谨,因而被上流社会称作“最优秀、最杰出”的人。然而,正是这个官僚队伍中的“优秀人物”,却是一个僵化的、生命意识匮乏的人。他的这一本质特征与渴望自由、不肯循规蹈矩、富有生命活力的安娜正好相反,而与那个僵死的、保守的和平庸的社会环境则恰恰一致。所以,卡列宁从内心深处难以接受安娜的生活准则,正如安娜难以接受卡列宁。他因为有环境的支持便总摆出绝对正确、居高临下的架势。他每每以社会所允许的宗教和道德规范逼迫安娜就范,给她设置种种障碍;他既不考虑自己的情感需要,也不考虑安娜的情感需要。在他这个把个体行为都纳入社会规范的人身上,跳动着的是一颗既不敢同外界抗争,又企图占有一切的猥琐、卑怯的灵魂。而安娜不仅艳丽迷人,雍容优雅,而且表里和谐,还以其精神的美而具有魅力。她真挚、单纯、自然、善良,同时又有旺盛的生命力,炽热的感情和一个“复杂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在卡列宁那儿安娜得到的只是形式上的虚无的婚姻。费尔巴哈论及爱情起源时也曾指出:“婚姻———自然是指自由的爱情结合,之所以神圣,乃是凭着它本身,凭着在今世所缔结的这种结合的本性。⋯⋯如果婚姻的纽带只是一种外在的约束,那就不是真正的婚姻,因而也就不是真正道德的婚姻。”(《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信仰与爱的矛盾》) 安娜生活在不幸的婚姻中,她追求新的爱情,正是要求平等的一种追求。
社会禁锢、大胆追求
安娜的爱情悲剧之气韵因时代与社会用法律、法规、教义丝丝入扣编织的罗网而浓重。安娜生活在19 世纪60-70年代,是俄国农奴制改革不久,旧的生活习俗、规章制度仍留有残余,新的行为准则, 生活方式尚未完全建立,“一切都翻了个身, 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从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历史大变革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向往美好爱情生活的安娜的心路历程与情感轨迹被烙上清晰的时代印痕。一方面, 新兴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思想使安娜看到了追求自由爱情幸福之路;另一方面,来自封建农奴制的残余势力处处设障碍,让这条道路怪石林立,瘴雨蛮烟。安娜在她还不懂“爱情是什么”的时候,由姑母做主嫁给了大她二十岁的卡列宁,对于天性纯洁善良的安娜来说,这桩婚姻的不幸就在于无情无爱的生活死水无澜,令人极度窒息。当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分到来时, 当社会一切旧有联系的松弛引起一切因袭观念动摇时,原本前卫的安娜女性的本质,渴望自由的个性找到了张扬的机会。同渥伦斯基的邂逅,是安娜追求爱情的契入点,她感觉到“时候到了,我要爱情,我要生活。”然而,在新旧错综交织的时代,在多数人多资本主义制度处于朦胧与恐惧状态之时,安娜的行为,必然遭际贵族社会强烈的反对与诋毁。她的一切行为都被视为违反家庭道德和社会教义的叛逆行为。特别是安娜面对彼得堡上流社会,是当时俄国经济不发展所造成的旧贵族与新的资产阶级的混血畸形儿。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带来的社交公开,给冷酷自私、假仁假义、荒淫无耻的官僚、伪君子、贵族相互勾引与通奸打开了方便之门。而旧的礼法大防,又迫使他们蒙上薄薄的顾全礼义廉耻的面纱。这样,就形成他们的可耻社交原则: 夫妻双方可各有情人,但不得公开,夫妻表面卿卿我我,背地勾心斗角,撒谎、欺骗、虚伪、淫荡充斥着整个社交界。因而,当安娜把她的爱情公布于上流社会,表明自己有爱的权利而离开她的法定丈夫的立场时,整个上流社会一片哗然。随之而来的是不贞不节、违反常规与体统、是真正的荡妇等等的污蔑、攻击与诽谤。而实质却是安娜内心的真诚与纯洁剥开了维系上流社会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肮脏与龌龊的遮羞布,是与社会界格格不入的安娜的挑战激怒了上流社会,安娜被拒之社会界已成必然。另外,当时俄国教会法律法规规定,离了婚的女人在丈夫活着的时候不可再婚,离婚后犯罪的一方也不可再婚。安娜要离婚已经很艰难,已被上层社会定了罪的安娜想要得到她所理想的爱情生活更是难上加难。没有社会支撑,单枪匹马的安娜在与强大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德观念相对抗时,她追求爱情自由的理念渗透的是无穷尽的苦涩,她寻找幸福的行为收获的只能是无奈与伤痛。安娜毫不掩饰、毫不自觉的把个人信仰、观念得释放和张扬,为她的爱情悲剧增添了更为浓重的悲戚的色彩。
林黛玉生活在女性“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强大的社会压力对于女性苛刻的要求,迫使女性意识觉醒。李纨自从丧夫后,正值青春的她本着“三从四德”的教义和社会得强大压力,“如同木头”一样过完了后半生,却深的当时封建势力代表贾母得赞扬;邢夫人厚着脸皮为自己的丈夫(贾赦)讨贾母的丫鬟做小老婆,真可谓把封建礼教做到了家。而林黛玉的女性观无疑与这种封建教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黛玉之诗《五美吟》提出来了一个重要的审美观念:“有才色”。黛玉对于红拂这个“有才色”、具有超乎寻常的政治才干,生命力旺盛的奇女子极为钦佩,而黛玉自己无疑也是才艺俱佳的典范,她与大观园其她女孩子一样成为作者女性美观念的体现者。这群“天真烂漫,相见以天”的少女与名缰利锁、庸俗浊奥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成为作者赞美、尊重的对象。无论是贵族少女还是丫头侍儿都同等地受到作者的尊重,并一起成为悲剧的承担者。尽管有阶级的分野,可作为一个女性整体,作为有才能有性情有品貌的人,她们都渗透着、表现着所谓“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的理想的人性美,使作者“忽念及当时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并发出“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的慨叹。这种观点既表明了作者对女性的尊重与赞美,表明了作者要求为女性争取权利与地位的尝试,也表现出一种与传统迥异的审美观。在他笔下,女孩不仅美在容貌,更美在性灵、美在情感、美在才华、美在品质。作者对女性美的这种理解,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社会的女性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序列完全排除了女子的真性真情;而不管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消极防范,还是主张“德才兼备”,赞成女性通过读书识字实行积极的自我奴化,其实都是对女性才能的否定。但红楼诸艳却大多才艺双绝,男人难以望其项背。尽管大观园中的女性很难走出三从四德的桎梏,甚至可以说,红楼诸艳中,还没有一个女孩子是在自觉地反对封建伦理教条,这一方面是因为清初社会现实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女性幽闭深闺,很难从社会上获得进步的思想养料与力量支持,但是,作者毕竟通过形象的故事抒发了对真情真性的赞美,对才智本身的肯定。因此,他所提倡的“才”便不会含有正统思想以“才”自封的含义。相反,这种“才”,这种真性情已蕴含了冲破三从四德的藩蓠的可能性,他甚至有可能不主张这一点,但他却忠实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伦理生活正在慢慢发生变化的某种消息。在作者笔下,这些女性都是可赞、可敬、可叹的与男性一样的人,甚至是比男性更优越的人,而不是满足男性欲望的性客体,更不是一个可供男性玩赏的物件。这是对男尊女卑的观念的反动,是一种萌芽中的平等观念。
这种观念正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的否定,正是对那种依附性的审美观念的反叛。而那种旧的审美观念作为传统女性观念的一部分,必然同样导致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并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黛玉对红拂的赞美,对西施昭君的同情,对绿珠的惋惜,与她对才色的肯定和她的恋爱生活一起表明,黛玉正探索着构想一种全新的两性伦理关系,她幻想在充分尊重对方基础上,以人的身份相互交往的两性关系,这种两性关系一定是平等的,相知的,有着共同的感情基础与思想基础的。
此外,女性意识觉醒仍有局限性
安娜与林黛玉等女性,都是在爱情的呼唤下,萌发女性意识,并为之追求。一、爱情至上。安娜和林黛玉视爱情为生命,衍变的终端却又是用我者去占有他者的全部空间。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安娜爱起来象火一样热烈,恨起来也象火一样能够烧毁一切。近乎疯狂的盲目使得她根本不审视群体环境对她的行为可能作出的强烈抵拒就把一见钟情迅速地发展成维特式的疯狂。非理性的冲动往往缺乏斗争的韧性,如夏天的雷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到头来,安娜最大的恐惧反倒不是上流社会对她的摒弃,而是她不知道她所爱的对象何时会停止这种爱,从而让她的全部牺牲彻底贬值———渥伦斯基既然可以慷慨地施舍给她宠爱,当然也可以合情合理地收回———当安娜卧轨自尽的时候,作为一颗敏感的心灵所体验到的现实处境,是一个人千辛万苦历尽磨难潜入险海深处捞取救命仙丹,最后却发现捞取的原来是不名一文的劣石一样万念俱灰。林黛玉的感情虽不象安娜这样外倾,但在表面的自我克制背后是加倍的理性弥散。没完没了的自虐,“病也病得奇怪,好也好得奇怪”的无常,最终将记录着生死恋情的诗绢抛入香炉,毫不犹豫地祈求死亡⋯⋯唯情主义的执着无明较安娜有过之而无不及。屠格涅夫说:“存在是一种自在的存在,而意识则是一种自为的存在。”一个人如果将个人幸福完全寄托在所爱的另一个人身上的话,如果这种寄托注定要落空的话,就必然导致个人追求在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的双重失落,因为现实的存在始终制约着自为的存在。二、物质生活不独立。林黛玉在大家庭里,吃穿用度全有人提供,从不用为自己的生计操心,在大观园那个狭小的范围内更多的试为生存现状得无奈与哭泣。安娜既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那种时代的最先进的、坚定地追求新生活的平民知识分子女性,也不是屠格涅夫笔下那种近似圣洁的追求着朦胧的理想的贵族少女,更不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那种没有接触过资产阶级文明的、精神世界备受压抑的保护国中产阶级妇女。”她貌似勇敢地将自我从贵族圈子里抽离出去,却完全不具左右现实命运的底气。在小说里,她孤立于她厌恶的群域外缘,毫无顾忌地嘲笑自己的丈夫是木偶,可就是这个在她眼里举棋不定、毫无人格尊严可言的“木偶”,只须一句“卑鄙!⋯⋯为了情人抛弃丈夫和儿子,却还在吃丈夫的面包,这才真叫做卑鄙!”,她的全部骄傲就土崩瓦解了。总之,由于安娜和林黛玉享受了太多的物质恩泽,她们便无从理解家庭和个人命运莫测的社会奥秘,她们的唯情更多地是昭示对旧生活的厌倦与脆弱。剥削阶级的寄生本性使得她们不可能成为推动时代变革的中坚力量。
纵观安娜和林黛玉追求个人幸福的全部历程,每一步心灵的演绎变化都可以说布满了唯情主义个人奋斗失败的身影———人类历史长河中为情而累、为情而死的女子何可胜数———安娜和黛玉的唯情主义虽然达到了个体反抗效能的峰值,但她们的结局却醍醐灌顶般告诫后人。
参考文献:
[1] 《红楼梦》原著,作者曹雪芹,成书于1784年。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婚姻悲剧为主线,描写了以贾家为代表的四大家庭的兴衰。提示了封建大家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表现了封建的婚姻.首先文化教育的腐朽堕落塑造了一系列贵族、平民以及奴隶出身的女子的悲剧形象,展示了极其广泛的封建社会和典型生活环境.曲折地反映了那个社会必然崩溃没落的历史趋势。
[2]《红楼梦》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作者王彩玲,发表于《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9期。作品分析了《红楼梦》中以林黛玉为代表的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和对于自由平等权利进行前所未有的关注。书中以林黛玉的诗《五美吟》为分析对象,展现了她的女性观,具有进步意义。
[3] 论《红楼梦》的女性主义价值诉求,作者翁礼明,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页码范围127-130页。作品阐释了《红楼梦》从女娲炼石补天和抟土造人的神话原型出发,对男性优越感、男性话语、男性权力结构实施颠覆,从而突破了中国文学史上延续了几千年的男性叙事模式,实现了张扬女性至上、女性至尊的女性主义价值诉求。
[4]林黛玉性格浅析,作者吴敏[1] 赵谦[2] 等,发表于《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3月第4期。作品中的林黛玉是一个典型的悲剧形象。林黛玉美丽的心灵、高洁的气质、纤细的感情、才情气质无一不表现出她的性格特点。林黛玉以其一生的眼泪控诉着这个暗无天日的社会对她不公平的待遇,并以死作出了最憾人心魄的反抗。林黛玉的美是典型的悲剧美。
[5] 满纸荒唐言,一曲女儿歌———《红楼梦》的女性主义解读,作者邓伟龙,发表于《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卷第6期,页码范围84-86页。文章运用女性主义的有关理论从《红楼梦》中对男性角色的处理和人物塑造等方面进行解读,认为男性是《红楼梦》中的退席者,贾母、凤姐是正位者,贾宝玉是个性别叛逆者,进而认为曹雪芹虽非一名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作家,但却有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一部《红楼梦》就是一曲女性的颂歌。
[6]《安娜·卡列尼娜》,作者列夫·托尔斯泰,本书通过女主人公安娜追求爱情而失败的悲剧,和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150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7]女性意识的萌芽与失落———再析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成因,作者张玉娟,发表于《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年01期,页码范围78-84页。文中从女性文学的角度看《安娜·卡列尼娜》,探讨了女性意识与女性角色的既对立又依存的关系。女性角色是社会习俗决定的,是附属于男性的,女性意识必须经由女性角色产生。安娜借助于伏伦斯基的爱情,重新认识了自我和周围的一切,她的女性意识开始萌发。由于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安娜与伏伦斯基缺少真正的对话,使得安娜无法协调自己矛盾的双重身份被迫自杀,这造成了女性意识的失落。托尔斯泰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女性地位,而是寻找社会和谐稳定的方式,所以,他从“爱的宗教”出发安排主人公的悲剧命运。
[8] 《论托尔斯泰对安娜身上女性意识的复杂态度》,作者赵海霞,《红河学院学报》2006年第4卷第1期,页码范围71-74页。作品分析托尔斯泰笔下的悲剧女性安娜既是一个大胆追求爱情自由与婚姻幸福的新女性,又是一个应受到谴责的有罪的抛夫弃子的坏女人,这反映了托尔斯泰对觉醒了的女性意识既有认同的一面亦有拒斥的一面,作者的创作心态是矛盾的、复杂的。从托尔斯泰对安娜的塑造中也流露出他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