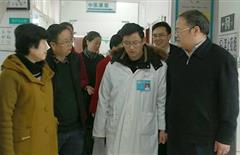微信每周美文
发布时间:2016-12-03 08:19:36
发布时间:2016-12-03 08:19:36
表演的美词
陆春祥
最近看过两回舞蹈表演。
一回在农村。六月中旬,我们去河北兴隆县的诗上庄,一个小村庄。诗上庄原来叫西凤庄,因农民诗人刘璋,从而策划成了一座充满诗意的村庄。这种诗意,当然是营造出来的。村道的岩石上刻有一些诗句,字用油漆血红涂着。村口有诗碑林,诺奖诗人、鲁奖诗人,好像开国际诗歌大会。村中小广场上,欢迎的人群,以中老年妇女和孩童为主,她们在炎日下舞蹈。舞蹈的队伍中,有一矮小老太太的舞姿,让我注目,她穿着低廉的彩服,两手捏着扇子,左右晃荡,不断扭着老腰,笨拙无序,和音乐的节拍,和众人的动作,几乎合不上。但她跳得很专心,并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很顽强地舞着。
另一回在渔村。七月下旬,我们到岱山的东沙,一个充满海洋咸味的古渔村。那几天的太阳,如烈火,即使在海岛,温度也在35℃以上。也有欢迎的人群,舞蹈,说书,越剧,魔术,渔妇街头织网表演,除了魔术在室内,其他都在室外。两把二胡,一把三弦,一个戴着耳麦的老人,古镇小戏台上,四人正在表演“走书”。说书老人着银色丝绸长袍,胸前已是一片湿透,他卖力地用岱山方言唱着,听了几句,不懂,我走到台上,看他面前有两张纸,上面写着“十劝世人”,噢,原来是规劝人们如何仁义礼智信的。
两回表演的场景,都让我感动。但我们私下交流说,更希望看到自然自在的场景。这是什么样的场景呢?人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在自家的屋子里,习诗吟诵,他们在街头做着自己的小买卖,他们自愿表演,但是随意率性,总之没有装饰的成分,菜园碧绿,鸡飞上树,村头的狗,会追逐着游动的人群汪汪。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我理解中的散文写作,也希望如此,大白话,简洁的,明确的,没有太多的伪装和架势。
芙蓉的美,在天然。看大自然中的那些花花草草,在茎芽初露时,稚嫩,无邪,即便长大,也大多本真,艳自有艳的遗传,淡也自有淡的家风,无论怎样,它们都朴素天然。
那些烈日下被动而机械的表演,尽管起劲卖力,反而给人以假,他们的日常生活,一定不是这样的别扭,尽管有人会付他们微薄的工钱。
我读大量来稿,经常发现这样两类稿子:一类写得天花乱坠,极尽美化之本事,架势似乎很足,奇句,异配,每段都有比喻,就如少数女子,每每出门,必定粉底打得极厚,口红搽得极艳,一般人很难窥见其真容,这是虚假的真实,犹如组织性的表演,不是自发自愿,并不耐看。另一类写得太实,老套路,老事件,语言陈旧,神情呆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将自己装在套子里,硬将丰富多彩的生活,过成天天豆腐咸菜的枯燥日子。这也是真实的虚假,就如小老太全身不协调的舞蹈,她要是坐在家门口,戴着老花镜,拿着绣花针,给小孙子绣个小肚兜,那该多协调呀。
字词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只是要协调,用合适了,就是美词美句。杜甫《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仅两句,战争的残酷,急促的征兵,官吏的残忍,百姓的痛苦,追奔呼号,悲怆愤恨。为什么要如此的生离死别?因为“新鬼烦冤旧鬼哭”、“古人白骨无人收”!有美词吗?没有,只是用了夸张的手法而已。
庄子曰:忘足,履之适也。
袁枚讲:忘韵,诗之适也。
我说,忘掉危险的美词美句,散文之适也!
一种深久的不安
乔叶
有时候,走在街上,看见穿得很破的收废品的老人,骑着锈迹斑斑的三轮车,摇着牛皮纸扎成的拨浪鼓,在绿草如茵的大街上,一脸灰尘,我就会觉得不安。看见卖水果的小贩,小心地拎起一串葡萄,把那些裂了口的果子仔细地摘下,然后把它们最大最好的那一面朝外码好,在深秋的薄暮里用芭蕉扇赶着聚拢过来的蚊蝇,我也会觉得不安。看见人力车夫坐在树荫下,寂寞地抽着烟,眼神却毫不懈怠地关注着来来往往的人流,仿佛要在第一时间的信息里捕捉到他们的乘客,我还会觉得不安。
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每月赚多少,有几个孩子,住在什么地方。除了从表象上对他们职业生活有一点认识,我对他们一无所知。可我就是无法抑制自己对他们的这种不安。他们也是有幸福的,我想。生意顺畅的时候,年节团聚的时候,雨天憩息在家里喝点小酒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快乐,也欣赏他们的享受,可我还是感到不安。而我不安的原因听起来竟是这样的矫情和可笑——因为我的物质生活比他们富足。
精神生活充满了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是不能比较的。我知道。可物质生活上我确实比他们富足。每当我掏出钱夹去消费时,就不由得会想到他们。一件专卖店里的名牌T恤,一道豪华饭店里的特色佳肴,一辆已经在路边等候的帕萨特出租车……每当我把目光投向这些昂贵的事物上时,总有些莫名其妙的忐忑和心虚,仿佛我在无形中欠了他们什么,而不能无所顾忌地去花这些其实是自己一分一角挣来的钱。
有很多人的物质生活都比他们好,也比我好,我知道。我只是平民百姓中的一分子。然而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有三六九等。我不是最低的一等,也不是最高的一等。作为最低等时,我一定不会甘心。但是当我看到真的还有那么多人在我的界线之下生活时,我却无法对自己理直气壮地说:“花自己的钱,想他们干什么,比你过得好的人多着呢。”
似乎是有些神经,有些自作自受。仿佛他们都是我多年以前的亲人,我今天的生活是踩在他们的肩膀上才拥有的。可细细想来,难道不是吗?我的上几辈的亲人中谁没有和他们一样在最狭窄的空间里挣扎过?谁不是和他们一样为了最基本的生计奉献着自己最浓稠的汗水?他们中有多少人敢去问津“梦特娇”的标价?有多少人摸过五星级酒店里的紫檀雕筷?有多少人会识别“蓝鸟”和“奔驰”的标志?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我怎么能够容许自己这么快就割断我和他们之间最本质的那种血脉关联?
我做不到。鲁迅说过,生存不是苟活,温饱不是奢侈,发展不是放纵。而我已经看到有太多的人正在奢侈和放纵中苟活着,我不想这样。我常常会问自己:有必要穿这么好的衣服吗?有必要吃这么贵的菜吗?有必要坐这么好的车吗?答案常常不是肯定的。那么,我就会坚定地和这些东西远离,去作一种最经济的选择。我不评价别人的消费。这是个性化的时代,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只尽力来控制自己,不让自己的欲望随着时尚的标准而高涨。仿佛只有这样,自己才不会离那些底层的人们更远,同时也让心灵获得最质朴的感知和最踏实的抚慰。
风雨南华寺
陈世旭
那一年,南雄关外的梅树著花未?那一月,粤北的木棉花是否格外烂漫?那一天,南华寺对面的大小山峰是否也像今天一样迷茫在烟雨?
弧形的南岭山脉,丹霞峰林起伏,曲江曹溪蜿蜒。曾几何时,来自天竺的僧侣“掬水饮之,香味异常,四顾群山,峰峦奇秀,宛如西天宝林山也”,预言“吾去后170年,将有无上法宝于此弘化。”677年,惠能如期而至,与预言相距175年。驻锡授禅凡37年,成《六祖坛经》。南禅一花五叶大播天下。713年,惠能坐化。其肉身成胎,夹苎塑成“六祖真身”。南华寺因之著称于世。旷达如苏东坡亦不免执着:“不向南华结香火,此身何处是真依?”严正如文天祥亦心向往之:“有形终归灭,不灭惟真空。笑看曹溪水,门前坐松风。”
我来南华寺,行走于迷茫。香客接踵,信众熙攘。燃烛跪拜者,多少人只为祈福,多少人诚心问道?莲花盛开,多少人花篮空空,多少人芬芳满心?来来去去,多少人依旧是迷人,多少人豁然贯通?
风雨如晦。心怅然。
达摩祖师一苇渡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五祖弘忍,额上三击,独立灵岩望江南,不闻鼓乐踏歌声。一声珍重,寒彻满天星。
成就圣者的路途一样坎坎坷坷。幼年丧父,砍樵奉母,也许贫寒离真谛最近。
破碎的皂袜芒鞋,在扬尘的乡野踉踉跄跄。褴褛的宽布大衣,在曲折的峡谷飘飘摇摇。身后是满含了杀机的追风,前面是来时已熟稔的故土。悄无声息地,圣者被遗落在林木茂密的湘粤褶皱。群星闪烁,野火远燃,新月从树梢落入潭底。圣者匆匆的步履浸渍晨露,晨露浸渍旅程。
荒园的野草枯了又生,穷乡的野花开了又谢,山雀子噪醒岭南岁月。竹林外幽幽一潭,盛着绿荷的阔叶。芭蕉在窗外颤抖,消磨了多少暗夜。茅檐泥墙下,雨痕是岁月的说明。没有香烟绕上殿宇,没有飞檐下的铃铛在午夜丁零。别后音书两不闻,遥知谣诼必纷纭。夜静兀自对残灯,谁识我,茫茫苦海任浮沉,无怨亦无憎。淡淡把旧页掩上,期待来日的黎明。
沉沦痴迷的众生,如同月亮背面的鸢尾,不被太阳温暖,也无法自我温暖。
唯有圣者超然。
听流水潺潺过庭前,看落叶寂寂飘阶下。斋堂里青菜豆腐和水煮,瓦檐下晨钟暮鼓答青磬。经书在案上翻动,念珠在指间轮回,袈裟飘忽在雨巷,菩萨微笑在莲座。没有孤独只有永恒,安详是直照心底的暖意。圣者千年的肉身沉寂在庙堂最暗的深处,却让觉悟的心灵一片灿然。
四千三百年
龙应台
太疼的伤口,你不敢去碰触;太深的忧伤,你不敢去安慰;太残酷的残酷,有时候,你不敢去注视。
厦门海外几公里处有一个岛,叫金门,朱熹曾经在那里讲学。在二十一世纪初,你若上网键入“金门”这两个字,立即浮现的大多是欢乐的讯息:“三日金门游”、“好金门3999元,不包含兵险”、“战地风光余韵犹存”、“炮弹做成菜刀,非买不可的战区纪念品”……知名的国际艺术家来到碉堡里表演,政治人物发表演说要人们挥别过去的“悲情”,拥抱光明的未来……
我却有点不敢去,尽管金门的窄街深巷、老屋古树朴拙而幽静,有几分武陵人家桃花源的情致。
金门的美,怎么看都带着点无言的忧伤。一栋一栋颓倒的洋楼,屋顶垮了一半,残破的院落里柚子正满树摇香。如果你踩过破瓦进入客厅,就会看见断壁下压着水渍了的全家福照片,褪色了,苍白了,逝去了。一只野猫悄悄走过墙头,日影西斜。
你骑一辆自行车随便乱走,总是在树林边看见“小心地雷”的铁牌,上面画着一个黑骷髅头。若是走错了路,闯进了森林,你就会发现小路转弯处有个矮矮的碑,上面镶着照片,已看不清面目,但是一行字会告诉你,这几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在那个钢铁一样的岁月里被炸身亡。是的,就在你此刻站着的地点。他们的名字,没人记得。他们镶着照片的碑,连做那“好金门3999元”的观光一景都不够格。
车子骑到海滩,风轻轻地吹,像梦一样温柔,但是你看见,那是一片不能走上去的海滩;反抢滩的尖锐木桩仍旧倒插在沙上,像狰狞的铁丝网一样罩着美丽的沙滩。于是你想起画家李锡奇,他的姊姊和奶奶如何被抓狂的士兵所射杀。他的画磅礴深沉,难道与疼无关?于是你想起民谣歌手“金门王”,十二岁时被路边的炸弹突然爆开炸瞎了他的眼睛、炸断了他的腿。他的歌苍凉无奈,难道与忧伤无关?
一九五八年的秋天,这个小小的美丽的岛在四十四天内承受了四十七万枚炸弹从天而降的轰炸,在四十年的战地封锁中又在地下埋藏了不知其数目的地雷。这里的孩子,没人敢到沙滩上嘻耍追逐,没人敢进森林里采野花野果,没人赶跳进海里玩水游泳。这里的大人,从没见过家乡的地图,从不敢问山头的那一边有多远,从不敢想象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这里的人,好多在上学的路上失去了一条手臂、一条腿。这里的人,好多过了海去买瓶酱油就隔了五十年才能回来,回来时,辫子姑娘已是白发干枯的老妇;找到老家,看见老家的顶都垮了,墙半倒,虽然柚子还开着香花。捡起一张残破的全家福,她老泪纵横,什么都不认得了。
在阿富汗,在巴勒斯坦、安哥拉、苏丹、中亚、缅甸……在这些忧伤的大地里,还埋着成千上万的地雷。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还生产着地雷,两亿多枚地雷等着客户下订单。埋下一个地雷,只要三至二十五美元,速度极快;要扫除一枚地雷,得花三百至一千美元,但是——地雷怎么扫除?一个扫雷员,冒着被炸得粉身碎骨的危险,趴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根测雷的金属棒,往前面的地面伸去。一整天下来,他可以清二十到五十平方公尺的范围。意思是说,要扫除阿富汗五分之一国土的地雷,需要的时间是四千三百年。
金门有一株木棉树,浓密巨大,使你深信它和山海经一样老。花开时,火烧满天霞海,使你想顶礼膜拜。
有时候,时代太残酷了,你闭上眼,不忍注视。
凝视达•芬奇
冯骥才
这个头戴飘翎帽子、满脸络腮胡子、长着鹰钩鼻子、生活在15世纪的意大利人,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
昏黄的灯光下,我远远望着这位很远又突然很近的意大利人——确切地说,是他的自画像。
画自画像的年代,他已经是熟透了的男人。看看他的眼神,如同地中海的海水,深邃中泛着莫测的光影。这种眼神,让人很容易联想起《蒙娜丽莎》的眼神,深含不露,波澜不惊,像迷雾里的烛光。
此刻,达•芬奇的自画像就在我的眼前。这个欧洲中世纪的男人,目光坚毅,鼻梁斧凿一样挺立,嘴唇饱满厚实,满脸的络腮胡须铁丝一样虬曲。画这幅画时的达•芬奇,生命和声誉如同冬日午后的阳光,可以沛然而从容地映照视野里的山川、河流、人物。一切都是壮硕健康的,整个世界仿佛一幅可以恣意涂抹的画布。而他为自己的头像选择了黑色的背景,黑得静穆而深沉,所有的景物和力量都蓄积在深重的黑色里,就连黑色的帽子也如同初开的黑色玫瑰,流溢着安详的静美。
在这沉寂的黑色里,一双眼睛摄人心魄。
达•芬奇的自画像令人一见倾心,不仅因为构图的独到、色彩的饱满、对比的精妙,更因为这一双奥妙莫测的眼睛。那双眼睛似乎凝视着你,凝视着世界,具有穿透力,又似乎只是在内视着自己,蔚蓝色的瞳孔里,映照出一生的风云、雷电、洪水、潮涌。
从这双眼睛里,可以看到《岩间圣母》里圣母爱意流淌的手势,看到《最后的晚餐》里,耶稣对12个弟子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出卖了我”时的表情各异。明暗对比的视觉效果,精细入微的情感表达,传递着画家的灵与性、爱与欲。
达•芬奇是以画家的身份闻名遐迩的,其实,作为画家,达•芬奇流传下来的画作并不多,壁画《最后的晚餐》、祭坛画《岩间圣母》和肖像画《蒙娜丽莎》是他一生的三大杰作。他本身是一个画家、文学家、科学家集于一身的传奇,他创作着美妙的寓言,设计着城市的建筑,研究着重力、元素和飞机的航行——他是一个上帝赋予人类的天才,有着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和表现力,他的一生像一支始终燃烧的蜡烛,照耀着人类文明的旅程。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临终前,他却无比惆怅地说:“我一生从未完成一项工作。”
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欲望贲张的时代,达•芬奇和他的作品,已经是经典的象征,是人类文明的象征,而真实生活中的达•芬奇终生压抑郁闷。
“主啊,我崇敬你,首先是由于爱,我应当忠诚地拥护你。”达•芬奇喃喃自语。
这是达•芬奇真实的内心独语。达•芬奇被恩格斯称为“文艺复兴巨人中的巨人”,他的身后是一片闪耀的辉煌。而他所有爱与生的纠缠,都被浓缩进了这双眼睛里,欲说还休,似笑非笑,直视着世界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