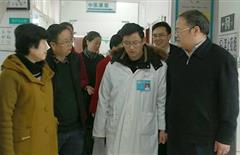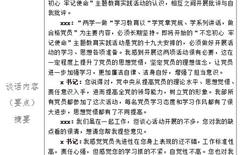假如自由能成为一种写作习惯
发布时间:2019-05-14 08:45:34
发布时间:2019-05-14 08:45:34
假如自由能成为一种写作习惯
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在座的同行交流。张庆国主编建议我有针对性地讨论女作家创作,接下来的时间我就以几位中国女作家冰心、丁玲、张爱玲、萧红的创作为例进行讨论,相对而言,大家对她们的写作比较熟悉,分析起来容易产生共鸣。在讨论之前,我想强调的是,虽然我关注女性写作,但我坚持认为,在艺术领域,优秀作品是不分性别的我们能说简奥斯丁是最好的女小说家吗?她的优秀不独属于女性写作领域,同理,我们也不能说鲁迅是最优秀的男作家。
不过,话说回来,因为历史文化渊源,相对于男性,一位女性在进行写作时,她有更多的障碍和束缚需要去克服,需要去挣脱。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书写、听从内心的声音,对于女性写作意味深长。我认为,自我解放、听从内心的声音是成为一个优秀女作家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一点,其他都无从谈起。所以,我给自己的发言起了个题目,假如自由能成为一种写作习惯。
一
今年三月,一位拍摄冰心纪录片的记者问我,为什么早期冰心的写作只是止于家庭,什么原因使她不如后来的那些女作家写得那么锐利。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回答起来也很复杂,因为影响一个作家创作特点的因素太多了。我只讨论影响她自由创作的障碍。《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是我的博士论文专著,它关注的是1895至1925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写作。在那本书里,我着重分析过冰心的创作。
冰心十九岁开始写作,很年轻就受到读者的欢迎。当时,她在创作谈里写过自己的创作习惯:这时我每写完一篇东西,必请我母亲先看,父亲有时也参加点意见。这句话好像随意说的,但研究者不能忽视。我们想,当一位女作家把她的父亲、母亲、弟弟们作为第一读者时,你能指望她抛弃乖女儿、好姐姐的形象?指望她进行越轨的创作几乎是空想,她的家庭教育不允许。而且,也是在那个创作谈里,她解释说小说中的我和作者不是一回事,她的母亲反问她:难道不是你写吗?当作家明知读者会对号入座时,她写作前会不会自我审查?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年轻的冰心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爱,小说中那种对优雅、纯洁女性形象的刻意塑造和克制讲述使她收到了雪片一样的读者来信,也受到了密集的赞扬。这些来信和夸奖来自大众和传统,它们对于冰心如何成为冰心女士起到了强烈的塑造作用,最终,这种力量内化为冰心的主体性格,进行写作的冰心女士有礼有节、温柔敦厚,从不越雷池一步。
这最终导致了冰心在叙事上的自我清洁,没有情欲,没有越轨,没有冒犯,在写作过程中,她心中始终有一个冰心女士,并且要尽力使她完美。所以,正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冰心完成了大众想象中的冰心,这是从两性关系中抽离出来的角色,它单薄、洁白,美丽、微笑,但也让人不满足。今天的研究者甚至尖锐地说,那个冰心女士不过是披着女性外衣的男性想象物。
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位广受关注的女作家,冰心这样写作也不是不可以理解,那是一种自我保护,她不想让人说三道四,她的家人也不愿意,所以,她可能也不得不如此。当一位女作家意识到自己的作品的第一读者是父亲、母亲和弟弟时,当她意识到万千读者都期待另一个她时,她会泯灭内心的另一个我。什么是不自由?这就是不自由。内在的自我限制、自我束缚、自我清洁使冰心的写作不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她能创作出一部与传统抗辩、与世界抗辩、对人们的阅读习惯进行挑战的作品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以,年轻的冰心写作只能如此这般。反倒到了晚年,冰心越来越犀利,越来越敢写,因为她开始懂得了解放自我、自由表达对于一位写作者的宝贵。
年轻冰心并不是个案。另一个例子是她同时代的黄庐隐,黄热爱写作,一直在《小说月报》发表小说。这个杂志喜欢书写社会问题的小说,庐隐一直坚持写这样的作品,工人,农民,贫穷者等等,她因此成为当时著名的女作家。但是,作为女高师的学生,这些人的生活之于庐隐是隔膜的,她最擅长写青年女性生存的困惑。而那又不是《小说月报》所爱,我们知道,主编茅盾非常欣赏庐隐关于社会生活的小说。今天看来,庐隐的小说并不成功,原因一则当然与天赋有关,另方面,为了编辑和批评家的趣味,她没有能真正打开自我。事实上,即使是写她的青年女性生活时,她也畏手畏脚,怕读者对号入座。
一百年来中国的女性写作史上,像冰心庐隐这样的女性写作者很多,她们身上未必没有成为优秀大作家的潜质,或者,她们也许可以写得更好,但是,最终没有能人尽其才,原因在于环境、道德以及内心对自我的束缚。
当然,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跟那时候已经有很大不同。可是,今天的我们真的能打开自我吗?真的能解放内心、不为世俗、不为文学趣味、不为批评家/读者好恶而写作吗?如果有人把这个问题抛给我,我肯定不能给大家满意的回答。流行什么写什么,是当下许多作者的习惯,至少我在杂志上看到的是这样,社会现实如此千奇百怪,但在作品里却千人一面:底层写作,日常生活的描摹,婆婆妈妈式人际关系,又或者,对社会问题的简单勾勒。能冲破当下写作氛围的作品很少,就我目前所见,鲜少有那种有独立判断力和穿透力的作品。我们的写作常常会被时代风潮、外界的看法、杂志的意愿所影响。
波伏娃在《妇女与创造力》中说:妇女是受条件限制的。她们不仅受从父母和老师那里直接受到的教育和限制,而且也受到她们所读的那些书的限制,受到她们所读的书包括女作家们所写的书所传给她们的那些神话的限制。她们受到传统的妇女形象的限制,而她们感到要脱离这种模式又是极其困难的。波伏娃说的情况现在恐怕依然存在,我们大部分人,在写作时是否想到过要冲破藩篱冲破教育的、世俗的、书本里有关好女人/好作家形象束缚?答案是否定的。
我想,大部分时候,我们其实是与这些规则和谐相处的,我们沉缅于好女人/好作家的规则中,以使自己适应这个规则。取悦他人,为身边习俗与惯例所困扰,是大多数女作者面临的障碍。作为批评家何尝也是如此。当我想到自己一篇论文要给某家杂志时,会要考虑到杂志的趣味,哪个段落可能这个杂志不喜欢。如果杂志不喜欢,我要不要修改?通常会的。还有,我的一个观点如果和我的导师、我尊敬的师长的观点不合,我心里会不会犹疑,又或者,告诉自己干脆不表达,沉默了之?最近几年,我深刻认知到,养成独立思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