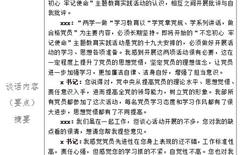棋王赏析《大智若愚的道和大巧若拙的白描叙事》
发布时间:2020-07-11 07:35:48
发布时间:2020-07-11 07:35:48
——《棋王》赏析
知识精英&普罗大众,艺术传授&民间衍生
西方阅读史研究非常关注普通民众的阅读,而不再将目光聚焦于精英分子。阿城的《棋王》就暗示着我们从知识精英的“我”,转向普罗大众一员的王一生的“创造性阅读”。当然,王一生的“阅读”采取了特殊形式“,阅读不应只局限于眼睛,戏曲、大书、图画就是文盲的书籍,听读书、听戏等以耳朵为主的活动一样也是阅读的形式”。
在去插队的车厢里,王一生听“我”复述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当《伤逝》中子君听涓生“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时只是默默不语、“微笑点头”,而王一生却随即发表“读后感”:“把一个特别清楚饥饿是怎么回事儿的人写成发了神经,我不喜欢。”于是作为讲述者的“我”有些不高兴:“那根本不是个吃的故事,那是一个讲生命的故事”……“读”同样的书、站在倾听者的位置(这个位置容易被理解为接受启蒙的一方),但是王一生并没有被动接受“我”对文本内容的讲述;甚至相反,在“我”所代表的自五四以来强调知识启蒙、精神性成长的“阅读”旁边,出现了王一生执拗的、抗辩的声音,由此充分可见阅读的能动性:阅读是一种读者主体性充分发挥的创造性过程;与作者一样,读者实际上也是作品的创造者。王一生“设身处地”地把自身作为“真实”而“理想”的读者,通过移情作用,来神会作品的主旨。
王一生对“吃”的高度重视,暗示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暗示精神超越的基点必须扎根于人类生活的血肉真实之中。王一生将“棋”与“吃”这两大嗜好并举,通向的是精神与物质的健全;他自我介绍时说:“一二三的一,生活的生”,这个名字不就在喻示一种整全合一的生活
当《棋王》中的“我”纠正王一生对《热爱生命》的理解——“那根本不是个吃的故事,那是一个讲生命的故事”———之时,想必充满了优越感(我们不要忘记,当《伤逝》中涓生发现子君的庸俗时,也指责“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部忘掉了”),“生命”对“吃”的轻视(并将此种轻视视作理所当然),正同于前引知识精英以一种合理性“压抑”另一种合理性的逻辑。然而文本必须经过读者阅读才能产生意义,通过对《热爱生命》意义的挪用 / 创造(关于饥饿、吃的故事),王一生及作家阿城,对上述偏至化的“压抑”逻辑表示了不满。
当然,阅读的能动性并非无限制的,王一生与“我”所彰显的不同“读后感”,显示了各自所受制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分野,同社会地位、教育背景、文化继承等多种因素紧密相关。而《棋王》最终显示的“我”向王一生及其所依凭的民间传统的尊重、归趋,敞亮了“文化寻根”、民间在当代文学中还原的意义“:由于传统文化的原初精神多已散失在民间,所以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探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民间的发现过程。寻根作家们在追求新的文学价值时,其实多半是把目光投向了未被意识形态内容遮蔽的民间文化,只有在这种非正统文化存在中才最大程度保留着民族自身的蓬勃生命力。”
由此再来理解小说中“棋”与“吃”的平衡,仿佛就像一个预言在昭示:知识者个人的精神探索只有紧紧地扎根于民间大地和人类生活的血肉真实与具体性之中,才能元气充沛而不至于陷入心力交瘁的“高处不胜寒”。
曾经有一种倾向认为,文化低级或朴质的中下阶层接受上层阶级传递下来的文化,如复杂精致的精英文化的故事情节经过通俗化演绎(通过通俗小说、戏剧、唱本等媒介)之后成为普通大众的读物,而下层阶级在接受这些读物的同时,也接受了上层阶级赋予这些文化内
容的意识形态。然而,《棋王》却告诉我们“,阅读一方面是一种控制,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发明与创造”,通过王一生与“我”的阅读实践,展示了特定时期中权力、社会阶层与文化内容之间的分异与整合。“现在看来,我们不能再把文化方面的变化看成是线性的、自上而下的或‘余波所及’式的。流变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可以向周边扩散,也可以向中心凝聚。”
题材
“具体说,《棋王》是立足于以庄禅为代表的古典本体论哲学的文化视角,借知青生活这一具体的生命现象为媒介,来探讨特殊年代里的理想人格与人生境界”。而阿城谈自己创作时说:“以我陋见,《棋王》尚未入流,因其还未完全浸入笔者所感知的中国文化,还属于半文化小说。若使中国小说能与世界文化对话,非要能写出丰厚的中国文化”。
《棋王》中阿城写道:“棋是道家的棋”。又说:“汇道禅于一炉”。真讲究造势,讲究弱而化之、无为而无不为,这是王一生的棋道,也正是道家哲学的精义。
王一生的道学写照:
【事件一】无论是浩劫中派仗冲突的烽火、大串联的狂热,还是上山下乡前的离情别意、搓跄岁月里的内伤外侮,都似乎未曾搅动他内心的平静
——他自有他的世界——“呆在棋里” ,心游神驰于棋盘上的咫尺方寸之间,不谙世事,不近流俗。那里没有恼人的权利和路线的纷争,没有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围扰。
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迷狂时代里,这种不迎不持、无动于衷的呆痴,这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消极,这种在“大而无当”中遨游的超脱,不正是对动乱现实的一种清醒认识和明智吗不正是不愿随波逐流、合污鼓噪的一种变相抗争吗道家哲学讲究从反面着手达到正面价值的肯定,所谓“将欲哀之,心故张之;将欲弱之,心故强之”就是这个意思。看来,阿城的本意是要写王一生的大智,写他在同辈青年中过人的聪慧,却故意先突出他的痴呆和顽愚,这不能说不是深得道家哲学强调对立面的转化和超越的妙谛。
【事件二】无视红卫兵纪律和农场规炬,独自徜徉江湖,在“野林子”里寻觅棋友和“异人”,可谓来去无踪,逍遥浪游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
王一生的“呆”,令人想起玄风道趣甚浓的文人骚客,如阮籍、稽康的颓,米莆的癫,倪攒的愚,黄公望的痴,李白的狂。他们都不随流,不合污,矢志弥坚,操守如一,有那么一般超然于世、物残双泯的痴迷。他们都不把艺术(象棋也是一种艺术)当成谋取外在功利的手段,而看成是解忧散怀、寄情养性的闲适和雅兴。
历史上的大画家、大画论家、大诗人所述达到和把握的境界常常都是庄子、玄学的境界。而棋王—王一生也不期而然地通向了庄子“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在忘我的宁静中进入自然的内部机枢并与之化而为一的境界。
【事件三】最终以下盲棋来作为终极对决
——“以神遇而不以目视”
棋赛的具体过程,阿城往往一笔带过;而刻画王一生下棋的精神面貌,却至为周详。“我”送水给王一生喝一节中关于他入神状态的精采描写,就颇得庄子“危丁解牛”、“轮扁断轮”的神韵。关于一个“瘦小黑魂”“静静地坐着”一段描写,更是冥合于老庄的玄远之境。最典型的是下面一段: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着眼看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象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
师承老庄美学的唐代艺术理论家张彦远所谓的“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正好用来作为王一生搏弈群雄的精神写照。
【事件四】视母亲留下的一副无字棋为生命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事件五】不屑给“脚卵”的父亲—一位国内名手当徒弟,却对一个棋艺非凡的拣废纸的老头顶礼膜拜。
——这些都渲染了他身上的玄思道趣。
【事件六】何以解忧,唯有下棋
——小说一再出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就自然把动乱现实和历史上的魏晋动乱联系起来,把王一生同“魏晋名流”和中国历代身处乱世的知识分子联系起来,使王一生形象具有了一种厚重的历史感。
这种追求超然忘我的解脱和个人人格的自由的精神,这种浸润着道家哲学的人生态度,正是中国历代身处乱世的正直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心态。为了变相抗世,他们往往远遁山林,寄情琴棋,以离世去俗之思抒忧世忧生之情;他们往往“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庄子。天下》)而佯狂假痴,口称“何以解优,唯有杜康”,意为“世人皆醉,唯我独醒”。
如此有民族文化背景的知识青年形象,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极鲜见的,这是阿城的特殊贡献。由此可见,新时期文学对十年动乱的反思,经历了几年的积淀之后,已经具有了更深广的历史容量;而知识青年题材小说突破的新信息,也由此传达出来。
作者的道学写照:大巧若拙的白描技法和结构形态
一种表现手法:如何通过一串精细的表面事物对抽象的意念作出明亮的皇露。他称这种表现手法为“呈现法”,亦即事物的原貌从其衣装里赤裸裸地跃出的感受力。作为读者,我们对小说苛求这种表现力,首先是苛求小说的文字具有这种表现力。
【事件一】……我拿出烟来请他抽。他很老练地敲出一支,舔了一刀;儿,倒过来叼着。我先给他点了,自己也点上。池支起肩深吸进去,慢慢地吐出来,浑身荡一下,笑了,说:“真不错。”我说:“怎么样也抽上了日子过得不错呀。”他看看草顶,又看看在门口转来转去的猪,低下头,轻轻拍着净是绿筋的瘦腿,半晌才说:“不错,真的不错。还说什么呢粮钱还要什么呢不错,真不错。……”
——通过“支”、“吸”、“荡”、“笑”、“看”、“拍”等一连串具体动作的白描,那种闲散浪游的情调与无所欲求的心境,以及与知心朋友重逢后的愉悦,再加上洗完衣服抽上烟后的轻松,都揉合世一起,构成了内涵难以言表的“不错”、“真不错”—岂止是“心满意足”而已!要突现人物那一刻复杂而微妙的心理状态,最好的办法是让人物保持在现实的关系网中的原生原态;而外在的主观说明和知性逻辑的介入,都难免会扰乱人物心态变化的真实姿态。
【事件二】“不瞒你说,我母亲解放前是窑子里的,后来大概是有人看上了,做了人家的小,也算从良。有烟吗”我扔过一根烟给他,他点上了,把烟头儿吹得红红的,两眼不错眼珠儿在盯着,许久才说……
——《棋王》的文字就很准确地捕捉了人物构成某一瞬间的心理真实与外部动作之间的独特的动态关系,以凝炼的笔墨加以具体描绘,而尽量避免了明显的象征、比喻和说明。这里,王一生那复杂、郁闷、难以言状的心境,阿城不渲染,更不夸张,只是极朴实地平淡无奇地叙述了王一生“突然打住”、“要烟”、“点烟”、“吹烟头”、“盯烟头”这几个连续的外部动作。没有一句说明痛苦、悲伤心境的文字,不涉主观,不带知性,却做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深得道家美学真谛的不动声色而富有弹性的表现方式,要比设释性的明说丰富得多,准确得多,形象得多。它给读者播下了弦外之音的种子,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
这与当今某些逞才使气、着意矫饰的青年作者大量错陈形容词,大量使用扭断文法脖子的欧化法相比,其明朗硬健的风格,尤为称道。他以拙重、凝滞的句法和硬瘦干涩的笔调,去契合那段动乱浑浊的人生,语言的外在律动与作品氛围的内在律动恰到好处地发生了共鸣,造成一种和谐、统一的,没有高光和亮色的基调,给人一种灰蒙蒙的历史感和往事感。有统一的基调,有真实的氛围,小说的世界就神韵畅通,灵气往来,就构成一个艺术的、生机盎然的第二自然。在这里,阿城的创作实践再次证明:大拙反成大巧,大愚却显大智。
【事件三】王一生对自己不能看电影、逛公园的苍白童年的回忆一也是不动声色的,讲到母亲临终只能用“捡人家的牙刷把”来磨的无字棋遗留给儿子时,一旁聆听的“我”也丝毫未插入动情的.评议,只是“鼻子有些酸,就低了眼,叹道:‘唉,当母亲的,。”而王一生也“不再说话,只是抽烟。”
——《棋王》不仅有意舍弃了跌宕起伏的戏剧性情节,甚至还有意将人物的内心冲突也深藏了。由于阿城在显露角色时,持极自然、超然的态度和毫不急迫的进度,不强调任何冲突,因此小说的结构显得那样平和、静态。这种毫无怨尤的痛苦,不大喊大叫’的悲伤,在无动于衷中“自然显示出的情感的净化,不仅反而更深沉、更感人、更震聋发绩,而且使整个作品的结构不是支撑在戏剧性的情节上,而是支撑在“寓动于静”的情感框架上。老庄说:“真哀则无声而悲,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庄子·渔父》)这种以静求动、以无见有的审美态度,也正是道家美学影响下中国历代文论的支轴之一。
【事件四】夜黑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王一生已经睡死。我却还似乎耳边人声嚷动,眼前火把通明,山民们铁了脸,肩着柴禾林中走,咿咿呀呀地唱。我笑起来,想: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倦意渐渐上来,就拥了幕布,沉沉睡去。
——《棋王》的结尾处,无论是王一生“有点什么才算活着”的感叹,还是“我”对“真人生”的体味,都没有说教的痕迹和知性的焦虑,仍然是中国式的那种“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的不涉语之境,含蓄蕴藉,意义丰厚。而“我”“拥着天幕,沉沉睡去”,则一切又归于静寂。这无声之处,这空白之境,却宣示了新的追求,拓展了新的意境,激起了读者更多的感悟。这种结尾的艺术处理,也通向了道家美学“无言独化”的妙境。、
王一生初从捡废纸的老头那听棋道,觉得“不象是说棋,好象是说另外的事”,就同《庄
子》中“危丁解牛”一类故事不象是在讲哲学、美学一样,《棋王》的妙处也在于:它似乎不刻意反映什么,似乎并无什么寓意,但却处处透露出对动乱现实的折射、对人生哲理的探求。“吃”的故事,“棋”的故事,构成了人生中物质与精神的两大部分,合成了生命的故事。虽是“奇文”,确具有了值得玩味的普遍社会意义。
《棋王》的时代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就誓把封建意识和文化一扫而清。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的,但他们难免也犯了“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的形式主义错误,把一切民族文化的遗产都纳入了清扫之列。这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刺激作用,同时也难免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因此,“五四”时期对我国传统文化缺乏深刻的辩证的清理和检讨,未能对传统文化作去粗取精的认识和正面价值的肯定,也缺乏对中西方文化作实事求是的比较研究、优缺点互补的气度。
但在事实上,纵向的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中积淀下来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特征,不仅不可能在横向移植的来势凶猛的冲击下彻底瓦解,而且仍然在源远流长地左右着我们对外来思维方式和审美追求的取舍。只有在大胆地消化西方文化的同时又不忘吸取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我们的文学才能带着中国民族的特有血脉,健壮地走向世界。
文学观念的弯擅,必将推动评论方法的更新。对于《棋王》一类明明在传统文化营养哺育下问世的小说,强行纳入西方批评模式中加以评说的作法,无疑都是一剂苦口良药。在人们普遍认识到了只有民族的才具有世界性之后,我们深信,随着我国当代作家民族意识的升华,创造性地运用我国传统美学与批评方法于当代文学研究,是应当提上议事日程并加以倡导的了。
与同时代青年主角小说不同
王安忆、孔捷生笔下的知识青年:在动乱岁月中总有着浓重的搅痛的自我意识和失落感,总是在努力追求自我在社会中的人生位置和价值。
叶辛笔下的知识青年形象:具有由下乡时的狂热到下乡后消沉、思考,再到新时期走向奋进的心灵轨迹和思想历程。
梁晓声笔下的青年:在“神奇的土地上”与“暴风雪”搏击的垦荒战士,那样敏感冲动,那样哀怨不平,那样悲壮可叹。
比较起来,王一生们显得要平和得多,知足得多,没有那么多强烈的外在欲求和内心挣扎。他们似乎并无狂热的理想,也无理想破灭后的悲哀,更没有这种悲哀积淀下来后的深刻思索。(须知,这一心理历程常常是不少同类题材作品所津津乐道的。)
不止王一生,文中的几个年轻人都显得平和满足。他们有“二十元钱”,能“强似讨饭”,“用不着找地方测夜”,就其愿已足了。”唯一的抱怨也只是农场里“脏兮兮”的,想“有个干净的地方住住”而已。王一生更进一步,不为外界的升降荣辱、贫穷富贵而苦心劳神,保持着内心的平静和自由。
这种中国传统诗画中常表现出的悠然意远、怡然自得的情绪在小说结尾处的一段感悟似的独白中表现得更清楚:“不做俗人,哪儿会有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白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丁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象人。”如前所述,在那个动乱时代,王一生们的这种人生态度,是洁身自好、不愿合污的一种变相抗争,而由此折射出的历史风貌和世态人情,则使小说具有了独特的认识价值。
当然,正如王蒙所指出的,“王一生的信条里确也存在着消极的东西”,他的“中国知识分子渊源久远的这一套乱世的自解的本领”,也“有其不足为训之处”。但我们的文学在纵情讴歌张志新式的乱世奋力抗争的人生态度的同时,也不忘为王一生们的人生态度作现实主义的描绘,这实在是“百花齐放”的又一可喜表现。
文化阐释
《棋王》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热潮之际,传统文化开始担起了当代文学的建设意义。不少人认为它呈现的是中国道家庄禅文化的内蕴、一种儒道相释的文化内涵。其中苏丁和仲呈祥1986年发表的《〈棋王〉与道家美学》应该是较早的从道家美学层面对文本进行阐释的,认为《棋王》是作者的一种“涤除玄鉴、澄怀味象”的审美选择。有人认为“王一生的棋道并不仅仅是道家文化的体现,其中又含着现代的精神,是一种东西方精神互相交融渗透而成的道”。还有人认为“阿城的小说《棋王》蕴含的文化意蕴不仅仅表现在儒道互渗的统一体中,同时在潜层次上还表现为一种世俗文化中的游侠的精神,一种与传统道德规范相冲突的精神,一种与寻根文学相联系的精神”。另有人对其进行现代性观照,黄伟林对《棋王》作现代性的解读,认为“阿城其实是看到了现代理性对人的异化,具体表现为人的馋与贪,表现为人对自己本质的迷失、本真的丢弃以及本分的逾越,于是他通过王一生的‘道的境界’为现代人的病态解毒,试图找回现代人那个本质、本真、本分的自我”。
其实大多数评论者更多的是带着寻根意识,在对王一生形象进行社会学、文化学或心理学等角度的阐释中,把其“吃”的生存哲学以及“棋”的文化内涵纳入被作者淡化的政治背景下,体现出他对人生苦难与社会现实的超越,表现出道家哲学平和、洒脱的人生态度和道家哲学中“无为而无不为”的理想人格。有的是着重论述文本所渗入的儒家思想和精神,认为阿城是以儒家的有所为态度进行创作的,这主要是结合作家生平经历和思想以及作品中王一生的对“天人合一”“执着坚定”“礼仪道德”的追寻进行思考的。而关于其中的游侠精神,则认为是由墨家学派演绎出来的。认为“《棋王》以王一生等人的生存方式、人生态度等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世俗文化精神,展示了作品在“文化寻根”中的追寻与思考”。
叙事技巧
叙述方位、叙述时间、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
认为作者把西方叙事学原理与寻根文化内涵巧妙结合了起来,用朴素的语言,简短的句子传达出王一生的精神世界,形成了作品淡泊、虚境、悠远的叙事风格,体现了庄禅精神旷达与超脱的美学思想。
【第一人称兼次要人物的叙述方式】
在叙述视角上,认为“作家阿城在《棋王》中运用第一人称有限知觉叙述者‘我’(目击者)来观察和叙述主人公王一生的棋道与处世之道,通过表层结构中主人公故事的发展来展现‘我’从寻道到悟道的过程这一深层结构,使在表层结构中处于故事边缘的‘目击者’成为深层结构中真正的主角,从而揭示出作品的深层内涵”。
这也正响应了阿城所说:“……《棋王》里其实是两个世界,王一生是一个客观世界……另外一个就是‘我’,‘我’就是一个主观世界,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客观世界跟一个主观世界的参照”。
有的牵涉出作家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作:“我们除了感受它浓郁的文化意味外,还将体味到作家阿城深沉、真切的人生体验无意中渗入了创作过程中,这种无意识趋向在深层里左右着他对《棋王》中‘文革’背景的处理,并极大丰富了作品内涵”。
【叙述顺序:顺序、倒叙及插叙的运用,以及省略与停顿的运用】
指出“在阿城的《棋王》中,省略的主要作用是:暗示了文本的历史时间;通过省略突出王一生的棋艺出神入化”。有的评论者在文本整体叙事的参照下,从阿城小说的欲望叙述策略及其当代意义进行分析,认为“阿城使得久违的道家文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得以正面呈现,并由此完成对欲望的重新叙述和话语转移”。
也有评论者在叙事方面对《棋王》进行分析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寻根作家的叙事策略本质上没有走出“文革”文学的话语霸权和叙事专制,寻根文学叙事策略显示着寻根作家对“文革”文学的超越和残留。”
对比分析
有些研究者就《棋王》与其他国内外经典进行比较,但是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物人生境界的解读。有的把阿城的《棋王》同台湾作家张系国在70年代创作的一部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棋王》进行比较,“从而探讨民族传统文化对作家作品的影响及意义,民族传统的思想意识,技与道的统一观念,描写观念美丑极致的同一”。
与国内作品比较:则如《〈棋王〉与〈水浒〉》,作者从两者的语言风格、饮食文化、场面布局以及人物形象进行比较,认为“阿城的《棋王》对《水浒传》从语言风格到布局谋篇都有明显的继承。《棋王》还继承了《水浒》主题的奋斗精神和对人生的追求,并形成了《棋王》自己的特定风貌”。
也有人在价值与反价值,寻根与反寻根,文化与反文化以及内部艺术特征上的一致性等方面把王安忆的《小鲍庄》与《棋王》进行比较。有的则站在传统文化救赎的角度把《棋王》与《阿Q正传》进行比较分析。与刘索拉的《蓝天碧海》的比较,是文化层面的“文化的个性与个性的文化”的比照。
与国外作品比较:把阿城的《棋王》与斯蒂芬·茨威格《象棋的故事》进行比较,认为二者有很多相似处,两者都是围绕“象棋”展开的。“从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层面审视作品和人物,可以看到,作家分别以灵魂的追猎和熔道禅于一炉的特殊方式展示了各自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揭示了人物命运的深刻的悲剧性,它们超越国家、民族界限而成为社会和时代的悲剧,其精神追求是不约而同的。”
而从中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影响下的人生观。有的人把加缪的《局外人》与《棋王》进行比较,认为“阿城的《棋王》同加缪的《局外人》一样,是一篇严肃的荒诞的哲理小说,它们的主人公不是以他们的行动向我们展开牵动着现实生活因果链条的情节,而只是漫不经心地、疲沓地甚至是有些痴呆地传达出他们的生活态度”。
而随着《棋王》被转化为影视作品,一些关于《棋王》的电影评价也应时而生,从“玩物与文化”的层面进行分析比较,比如与《海上钢琴师》的比较,“试图探讨在不同条件下,人们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以及工业文明给传统文化带来的巨大的冲击,从而引发对现代生活幸福观念的思考”。
在“吃”中乐天知命,又能在“棋”中倾力一搏、为社会主义新人所需的精神气质
首先,把《棋王》列入知青文学是不得要领的。这部作品的主旨之一,是在树与藤、水与月一般缠绕、交映的现实世界(生道)和艺术世界(棋道)之间,借棋王的‘瘦小黑魂’抒发深沉的历史感。
《棋王》发表时,人们曾为它的冷峻所惊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有多少离愁别绪曾被许多浓墨渲染过。但是,阿城似乎对这类情绪缺少兴趣,这就使他一扫别人的情调,写出了自己的境界。列车就要启动了“车厢里靠站台一面的窗子已经挤满各校的知青,都探出身去说笑哭泣”,而“我”却平静自如;别人都把这一离别当成“风萧萧兮易水寒”,而“我”却认为“此去的地方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我便很向往”,甚至担心“每月二十几元,一个人如何用完”王一生比“我”还要超然物外,他满有兴致地找“我”下棋,对眼前的情境视而不见。在这种情调和人物性格的描写中,体现出阿城对世态人生的庄谐并作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