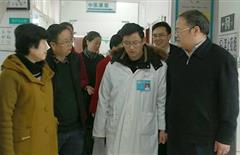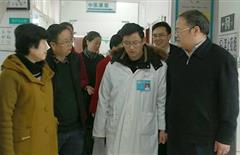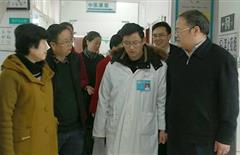生命所不能承受的轻
发布时间:2011-11-27 11:53:08
发布时间:2011-11-27 11:53:08
生命所不能承受的轻
尼采常常与众哲学家困惑于一个“永劫复归”的观念。回味我们生活中曾发生的事情吧。一旦它们往复一日的重演,其那永无休止的本身,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近乎癫狂的幻念。
从反面说:“永劫复归”的幻念表明,那是已经不复存在的生活,即使没有了踪迹,便如同影子不具有分量一样。恐怖也罢,美丽也罢,崇高也罢,一切物质都随其本体的消失而失去了意义。他就像十四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战争,既然没有把世界命运改变,哪怕有十万黑人在战火的吞噬中灰飞烟灭,我们也不会对此过分的在意。
然而,如果,十四世纪的两个非洲部落的战争一次次重演,会给战争的本身带来变换吗?
会的,它将变成一个永远的硬块,再也无法归复自己就有的虚空状态。
一旦法国大革命的旧页不断在重演,法国的历史学家就不会对罗伯特 斯庇尔颇感自豪。正因为它们的故事不在重演,革命的浴血年代被重现于文字。理论以及各种相关的研讨都轻于鸿毛,无法对任何人构成威慑。这个历史只出现一次的罗伯特 斯庇尔,绝不同于那个永劫复归的罗伯特 斯庇尔。后者的存在将以法国的生命为代价的。
于是,我们这种“永劫复归”的观念里隐含这一种视觉,它改变了我们自以为相对熟悉的和确定的事物,抹去了事物一闪即逝的轻松感和对环境缓解作用。能让我们更容易的定论,我们如何去谴责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往日的都不存在了我们只能在回忆的碎片里拼凑出依稀的概念,包括生死离别,用此来判别一切。
不久前,我察觉自己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体验,我翻阅了一本关于希特勒的书,在书里的字里行间以及对其照片的直观感受下,我想起我的童年。这一段浸满悲痛,不堪回首的回忆,但较之于我在不断的回忆中这份沉甸甸的承担,我觉得死亡亦是一种解脱。
或许因为历史书的缘故吧,我对希特勒有了一种仇视,但现在这种仇视已经逐渐的模糊了,这暴露了一种我们道德上的一种无限的堕落。我们的世界合理的存在着,是基于一种不存在的物质,在这个世界里人们预先把一切都原谅了,因为一切皆可笑的预先被允许了。
如果我们的生命每一秒都在周而复始的重演着,我们就会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永恒所困。这个前景里注定不在拥有重复的生命,在那永劫复归的的世界里,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将承担着超重。这或许就是尼采说的永劫复归现实中最沉重负担的根本理念吧。
如果永劫复归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在你我的生活中呈现出来是一切辉煌的轻松便是与之抗衡的最有力的借助。
最沉重的负担使我们沉陷之至塌陷,然后一蹶不振。可是在恒久不变的爱情诗篇里。女人在被裹在男人的身下是才会最能感受到灵与肉同在的安全与舒适。也许最沉重负担的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充实的象征。负担将我们的生活压近大地,同时也走向了真切和实在。
相反把负担卸下人身自此可以身轻如燕,甚至可以轻松的挣脱地心的吸引和束缚。如果我们选择离别了大地,便毫无疑问的选择离别了真实的生活。伴随着自由的得到,运动却失去了意义的目的。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选择呢?沉重还是轻松?
巴门尼德于公元前六世纪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眼中的世界同时具有两种对立的景象:明与暗,雅与俗,寒与暖,存在与非存在,他把其中一部分称为积极,另一部分称为消极。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积极与消极的两极区分实在不能称之为具体的深刻,至少我们还可以确定积极与消极之间谁更轻松,谁更沉重。
巴门尼德的回答是,积极就是轻松,消极就是沉重。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疑虑尚存,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轻松与沉重相对,是最难解也是最模棱两可。至于现在的我们怎样选择,那就要看这个人的文学观和生命的胸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