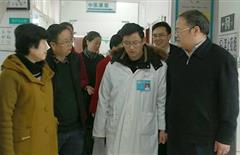实证科学的哲学根据和逻辑前提
发布时间:2018-09-26 17:43:42
发布时间:2018-09-26 17:43:42
实证科学的哲学根据和逻辑前提
实证科学的哲学根据和逻辑前提
2015-07-12 19:56:46思辨科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理论学术”,它包括数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三个部门。亚氏称其中形而上学为“第一哲学”,故其“理论学术”一语与“哲学”具有同等意义。亚里士多德所谓“理论”的意思就是:不为实用目的,只是为求得真理而论究事物的原理和原因。
形而上学如何论究至理极因?据培根在《新工具》中的概括性论述,他的形而上学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分野在于获取最普遍原理的方法不同:前者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达到最普遍的原理”,后者则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越到最普遍的原理,其真理性即被视为已定而不可动摇,而由这些原则进而去判断,进而去发现一些中级的公理”。由是观之,“理论”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具体意义是指:为求得至理极因所开展的形式逻辑思维和相应的论理过程。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摘“玄学”(形而上学)时所说的话来讲,“玄学”的“理论”特征在于:“高翔于经验教导之外”,“唯依据概念”来进行“完全孤立之思辨”。
要之,按形而上学固有的特性来说,它是这样一门学问:以脱离经验的纯粹逻辑思辨来推求至理极因的理性学问。“形而上学”一词在用法上从一开始就有两种基本指向:一是在认知对象的确定上指向终极存在,一是在认知方法的确定上指向纯粹理性。中世纪经院哲学也依然是从这两个方面去理解形而上学的,这突出地表现在经院哲学大师阿奎那在把主要研究上帝的神学纳入“思辨科学”范畴的同时,又称它为“形而上学”,其语意指向非常明确:上帝,终极存在之实体也;思辨,纯粹理性之表征也。
古希腊和中世纪的形而上学具有两个方面的共性特征:在认知对象上探求至理极因,在认知方法上采用逻辑思辨。据此,可从两个方面去理解这种古典形而上学的学术性质:从学术对象方面去理解,它是关于至理极因的宇宙论;从学术方法方面去理解,它是关于逻辑思辨的知识论。
西方古典形而上学宇宙论所论究的是全宇宙的原理和原因,这种探究至理极因的宇宙本体论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哲学本体论,一种是神学本体论。古希腊的宇宙本体论是哲学本体论(早期形式为自然哲学形态),中世纪的宇宙本体论是神学本体论。
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知识论也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以论辩术为研究内容的辩证法,一种是以演绎法为研究内容的逻辑学。辩证知识论主要是古希腊智者学派所研究的,逻辑知识论主要是亚里士多德所研究的。古希腊哲学晚期的斯多葛派则把辩证法和逻辑学视为同一个东西,认为它们都是研究人类理性的学问。
亚里士多德所创制的演绎法是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知识论研究的最高成果,它不只是形式逻辑思维中的一种推理方法,同时还具有如下知识论意义:首先,它标志着一种知识本体观和与之相应的关于各个知识部门之间相互关系的知识等级体系观;其次,它标志着一条立基于这种知识观念的由普遍到特殊、由一般到个别的认知路线;再次,它标志着一种较低级知识部门依据较高级知识部门所提供的通则(普遍知识、一般知识)来获取自己的知识(特殊知识、个别知识)的认知方法;第四,它标志着一个由某些规则所构成的逻辑系统和由这些逻辑规则所决定的特殊思维方式与论理方式。
西方形而上学知识论所最为重视的是逻辑认知。所谓逻辑(logic),按其本义来说,就是关于论理规则的学问。不同的逻辑系统有不同的论理规则,但它们都是为求知者所制定的其认知世界的思想活动所应当遵守的思维规则,在其现实性上,就是认知群体交往中主体际认知对话所应当遵守的论理规则。所谓逻辑认知,就是求知者在一定的论理规则系统中通过合乎其规则要求的有序的认知对话来实现其求知活动的求知方式。当初亚里士多德创制演绎法,是在不抱有“任何实用目的”,纯粹“为求知而从事学术”的“自由学术”环境中进行的,他提供这样一套论理规则系统,其实是完全站在认知主体的立场上,不考虑实践主体的实用要求,只考虑认知主体的求知要求,以之服务于认知主体的交往活动,规范其认知交往中的论理活动,以求其主体际认知对话的有序进行。这套论理规则系统直至弗兰西斯.培根发明“新工具”才被革命性地超越。
西方形而上学知识论的上述特点反映出它的本体论的旨趣在于关心和探讨与逻辑主体相关的本体问题,以至于可以将其本体论归结为逻辑主体论。以逻辑主体论为旨归的西方形而上学本体论所探讨的本体问题的实质在于:人类追求真理所依凭的那些逻辑形式的理智法则究竟是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亦可表述为:究竟谁为人的思维立法?
在思辨科学时代,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形而上学认为,人的思维的最终立法者必是“创作第一级单纯永恒运动,而自己绝不运动,也不附带地运动”的“不动变本体”——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基本实是”、“第一原理”。在亚氏的演绎逻辑认知框架之内,人们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越到最普遍的原理,其真理性即被视为已定而不可动摇,而由这些原则进而去判断,进而去发现一些中级的公理”。这个一经发现即被视为具有牢不可破的真理性的最普遍原理以及那些中级公理,便是西方古典形而上学所理解的并且被它看作人类思维依据的逻辑形式的理智法则。
要而言之,在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看来,人类的理智必须借助于形式逻辑(演绎逻辑)法则才能求得真理。直到西方学术进入所谓“实证科学时代”,这种形而上学观念才被革命性地超越。
信奉“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站在实践主体的立场上,本于追求“新事功”的实用目的和出于对实践主体“对新事功的发现”之渴求的理解,贬斥从事“自由学术”的人们的逻辑思辨活动,批评其“由论辩而建立起来的原理,不会对新事功的发现有什么效用”,指摘他们不过是“使用这种已被公认的哲学或其他类似的哲学来供争论的题材,来供谈话的装饰,来供教授讲学之用,以至来供生活职业之用”。而“我所要提出的哲学是无甚可用于那些用途的”——培根要提供一种“对新事功的发现”有效用的“新工具”,其归纳法正是在这样一种“实用学术”环境中被创造出来的。培根的归纳法也是服务于主体际认知交往的论理规则系统,特其不像传统演绎逻辑那样是服务于脱离实践的纯粹认知主体的交往活动,而是服务于实践主体的认知交往,即前者是规范纯粹认知主体论理活动的思维规则体系,后者是规范实践主体论理活动的思维规则体系。
培根的归纳思维规则体系是以其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作为基础的。培根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也是以逻辑主体论为旨归的,它所探讨的本体问题同样可以被表述为“究竟谁为人的思维立法?”只是其答案不同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形而上学本体论。在培根看来,人的思维立法者是自然界本身,而不是某种超自然的东西(如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不动变本体”、基督教形而上学中的“上帝”之类);人只有发现了自然界中“那种永恒的、不变的法式(至少在理性眼中看来和就其本质的法则来说是这样的)”,才能“在思辨方面获得真理,在动作方面获得自由”,科学“在隐秘结构的全部发现方面,也须求之于始基的原理才能见到真正的和清晰的光亮,那始基原理是能完全驱除一切黑暗和隐晦的”。在培根的归纳逻辑认知框架之内,作为自然界中决定个体事物“简单性质”的基础和“若干最不相像的质体中的性质的统一性”的“自然的永恒的和基本的法则”的发现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达到的:“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达到最普遍的原理。”
由此可见,培根的归纳理论内在地蕴含这样一种自然观:自然界的规律(培根称之为“永恒的、不变的法式”或“本质的法则”、“原理”等)有特殊规律与普遍规律之分;特殊规律寓于可以为感官所感知的自然现象(培根称之为“特殊的东西”)中,普遍规律寓于特殊规律中,最普遍的规律则寓于较普遍的规律中。这种自然观非常明确地肯定了自然界有一个最普遍的规律,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受这个规律的支配,即肯定了自然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同时还肯定了在这个普遍联系的世界中客观真实地存在着特殊与普遍既互相区别又互相统一的辩证矛盾关系。从形式逻辑的观点来看,这种辩证的自然观是实证科学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和充足理由,因为按照形式逻辑的演绎规则,实证科学这个特殊事物,在它之上理应有一个普遍原理或一般原则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和根据,而上述辩证的自然观恰恰为实证科学提供了一个普遍原理——特殊与普遍的辩证矛盾原理,正是根据这个原理,才能从理论上推演出实证科学是必然可能从而足能成立的结论来;反之,如果认为这个原理本身是虚假而不真实的,则同样可以从理论上推演出实证科学是不可能从而无法成立的结论来。
事实上,实证科学的认知本质就是在于从关于个别存在(自然现象)的经验知识上升到关于一般存在(自然规律)的理论知识,再通过实验来检验理论知识之是否具有经验上的正确性(真)和事功上的实用性(善)的过程。因此,如果不承认自然对象世界中客观真实地存在着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辩证矛盾关系,这就必然要导致否定自然知识世界中个别(经验形态的自然知识)与一般(理论形态的自然知识)之间存在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贯通从而可以互相转化的辩证矛盾关系,乃至根本否定区分经验知识与理论知识的必要性,从而取消经验知识与理论知识的互相转化问题,如此一来,在形式逻辑意义上,实证科学的认知过程便不再是有可能和有理由进行的。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形而上学,固然也肯定宇宙之间有一个最普遍的原理,这似乎也意味着是肯定这个世界的普遍联系,但是,不仅这个原理是外在于自然界的,是超自然的宇宙本体,而且一旦获得了关于这个宇宙本体的知识,“其真理性即被视为已定而不可动摇”,这意味着在认识上它无需加以经验的证明,并且这种所谓的真理性知识是“由论辩而建立起来的原理”,它虽然也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出发”,但“对于经验和特殊的东西只是瞥眼而过”。(参见培根:《新工具》,第12-13页)所以,在古典形而上学的知识世界里,关于特殊的东西的经验知识和关于普遍的东西的理论知识之间本质上并不构成一种彼此可以互相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由此也说明了,它所肯定的世界的普遍联系并不具有辩证性的特点,这种联系本质上是超自然的宇宙本体与自然界之间的外在联系,在这种联系中,自然界处在受宇宙本体绝对支配的被动地位,因此,存在于这种联系中的普遍与特殊,只是特殊无条件服从普遍的单向关系,这种关系当然无涉于辩证法。
与古典形而上学不同,培根的形而上学是一种经验哲学形态的现代形而上学,它自觉地要求哲学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因而具有自然哲学性质。这种哲学所肯定的普遍联系根本不同于古典形而上学所肯定的那种普遍联系,它的自然观与知识观是互相统一的,故不仅其自然观是辩证的,其知识观也是辩证的,即它不只是肯定自然对象世界中个别(自然现象)与一般(自然规律)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时也肯定自然知识世界中个别(经验形态的自然知识)与一般(理论形态的自然知识)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且它的辩证的自然观是通过其辩证的知识观反映出来的,这种知识观一方面肯定经验知识有必要向理论知识发展,“从经验来抽出和形成原理”,这是确定经验知识可以向理论知识转化;另一方面又肯定理论知识有必要加以经验的证明,“从原理又来演出和推出新的实验”,这是肯定理论知识可以向经验知识转化,肯定观念形态的知识可以向现实形态的实践转化。[1]
这种辩证的知识观反过来确证了其自然观的辩证性,表明这种自然观所肯定的普遍联系确有辩证性特点,即它不是一种单向的特殊服从普遍或普遍服从特殊的关系,而是彼此相互区别、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辩证矛盾关系。正是由于自然界客观真实地存在着这种辩证关系,关于这种客观的自然辩证关系的知识,才也可以相应地区分为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并且这两种知识也相应地存在着相互区别、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辩证矛盾关系,因而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1]参见培根:《新工具》,第117页。按:《新工具》译者许宝骙先生在此作译注道:“由这里可见培根并非只注重归纳法而忽略演绎法;也可测知培根所想的演绎法不是抽象的,而是根据抽出和形成的原理来演出和推出新的实验,——只是他从未把后者加以阐论罢了。”(培根:《新工具》,第117页,译者注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