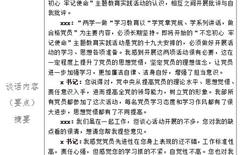胡萝卜须
发布时间:2018-06-30 01:17:35
发布时间:2018-06-30 01:17:35
胡萝卜须
[鸡]
“我敢打赌,”勒皮克太太说,“奥诺里娜又忘记把鸡窝关上啦。”
可不是,人们只要从窗口一看,那边,那大院子尽头,鸡窝像个黑洞清清楚楚的浮现出来。
“费利克斯,是不是你去关一下?”勒皮克太太对她三个孩子中间最大的一个说。
“我可不是管鸡的,”费利克斯说,这孩子脸色苍白,没精打彩的,胆子很小。
“那,你去,埃内斯蒂娜?”
“啊!我吗,妈妈,我害怕!”
大哥费利克斯和姐姐埃内斯蒂娜回答着,头连抬都不抬一下。他俩几乎额头碰着额头,都伏在桌上看书,兴趣正浓。
“唉,我多傻!”勒皮克太太说。“我刚才怎么不曾想到呢,胡萝卜须,去把鸡窝关上!”
她给她最小的孩子取了这么个好名字,因为这孩子的头发是赭红的,皮肤上有不少雀斑。胡萝卜须,这时正在桌子底下玩。他站起身来不好意思的说:
“妈妈,我,我也害怕。”
“怎么!”勒皮克太太答道,“这么大个的男孩子,还怕呢!开玩笑!给我快去!”
“大家都晓得的,他像山羊那样胆大。”姐姐埃内斯蒂娜说。
“他什么都不怕。”他大哥费利克斯说。
这些表扬的话使胡萝卜须感到挺自豪,反而觉得要是够不上格倒是个羞耻,他思想里已经在跟怯懦做斗争了。为了进一步激励他,他妈妈说要他再不去,就赏他一个耳光。
“至少,点个火照照我。”他说。
勒皮克太太耸了耸肩头,费利克斯轻蔑的笑了笑。还是埃内斯蒂娜可怜他,拿了支蜡烛陪着小弟弟走到回廊尽头。
“我在这儿等你。”她说。
一阵狂风吹得烛光直晃,灭了,她立即畏缩的逃了回去。
胡萝卜须两腿贴得紧紧的,寸步难移,在黑暗中直打哆嗦。夜那么黑,简直伸手不见五指。有时刮起冷风,像一块冰毡似的,团团把他围住,几乎把他卷走。有多少狐狸,有多少恶狼,在他手指缝里,在他脸上吹气?最好还是一头朝估计是鸡窝的那边猛冲过去,冲破这片黑暗。他摸索着,终于抓住了鸡窝的门把手。那群鸡一听到孩子急急促促的脚步声,惊慌得骚动起来,在蹬架上咯咯直叫,胡萝卜须一边对着他们嚷嚷:
“别叫啦,是我!”
一边把门关上,胳膊啊,腿啊都像长上了翅膀似的,溜了回去。当他气喘吁吁的又回到又暖和又明亮的屋里时,他觉得非常自豪,仿佛他浑身粘满泥浆的湿衣服顿时换上了一身新装。他微笑着,骄傲地直挺挺的地站着,等别人祝贺,好了,现在没有危险了,他眼睛紧盯着亲人们的面容,想从那里寻觅他们刚才为孩子而焦灼不安的痕迹。
可是大哥费利克斯和姐姐埃内斯蒂娜仍然平静的在看他们的书,勒皮克太太用她那自然而平静的声调说道:
“胡萝卜须,以后你每天晚上去关鸡窝的门。”
[鼹鼠]
胡萝卜须在路上碰到一只鼹鼠,那样子黑得像个通烟囱的。他拿来玩了半天,随后他想弄死它。他把它抛向空中好多次,巧妙地抛掷上去,但愿它掉在一块石头上。
起初,进行得很好,很顺利。
鼹鼠的脚全折断了,脑袋开了花,背脊也碎了,它的生命似乎并不坚强。
后来,胡萝卜须发现它还没有死,这真吓得他目怔口呆。他把它抛过屋顶,抛上天空,随便怎么抛鼹鼠还是不死。
“该死!它不死。”他说。
果然,在那块溅着鲜血的石头上,鼹鼠给砸得稀烂。它那满是油脂的肚子像一块冻子似的颤动着;从这阵颤动中仿佛看到了生命的幻象。
“该死!”胡萝卜须狂热的叫起来,“它还不死!”
他把它捡起,辱骂着,于是又改变了方法。
满脸通红,眼睛里含着泪水,他在鼹鼠身上唾了几口,再提起来,用尽平生气力扔到石头上。
可是那难看得肚子还是不住的颤动。
胡萝卜须越是像发了疯似的拍打,鼹鼠越不像死的样子。
[奥诺里娜]
勒皮克太太:“你今年究竟多大年纪啦,奥诺里娜?”
奥诺里娜:“过了诸圣节(*1)六十七,勒皮克太太。”
勒皮克太太:“你已经这么老啦,我可怜的老婆子。”
奥诺里娜:“只要能干活,老又算得了什么。我可从来不生病。马也没有我这样结实。”
勒皮克太太:“我想跟你讲一件事,好吗,奥诺里娜?你可能会突然死掉的。某天晚上,你从河边回来,你会感觉到你的背篓比平日压人,你推的那辆小车也不过去沉重难推;兴许你一下子就倒在地下,跌倒在辕把中间,鼻子紧贴在刚洗过的衣裳上,你就完了。等到别人把你扶起来的时候,你已经断气了。”
奥诺里娜:“你在跟我说笑话,勒皮克太太。你甭怕,我手脚还麻利着呢。”
勒皮克太太:“你开始有点驼了,说实在的。不过背脊弓下来,洗衣裳时腰反而不觉得吃力。可惜你的目力不济!你不必否认,奥诺里娜!这些时我早就看出来了。”
奥诺里娜:“啊!我看东西非常清楚,还跟我出嫁的那辰光一样。”
勒皮克太太:“好!你去把碗橱打开,随便拿一个盘子给我。要是你把餐具都擦得干干净净的,哪里来的这些水气?”
奥诺里娜:“碗橱里潮湿”
勒皮克太太:“难道说碗橱里还有谁的手在摩挲盘子?你瞧瞧这个手印。”
奥诺里娜:“你说哪里有,太太?我一点也看不出。”
勒皮克太太:“我要责备你的就是这个,奥诺里娜。你听我说,我并不是说你懈怠,要是那么说,我就错了;像你干活这样麻利的女人我在本地还没有见过;我是说你确实老了。我吗,我也老了;我们都老了。光是好心好意,那不够。我敢说你一定常常会觉得眼睛上有一层轻纱罩着吧。你用手揉也没用,总还是模糊。”
奥诺里娜:“不过,我能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昏沉不舒服,就像头浸在水桶里那样。”
勒皮克太太:“不,不,奥诺里娜,你可以相信我。就在昨天,你还拿了一只脏玻璃杯给勒皮克先生。我怕一提会让你难过,所以我当时什么也没有说。勒皮克先生,他也什么都没有说。他话是不说,可什么事也逃不过他的眼睛。别人以为他遇事漠不关心:大错而特错。他洞察一切,什么事情都铭刻在他脑海里。他当时只是用手推过你拿的那个杯子,硬是吃午饭时没有喝酒。我为你难过,同时也为他难过。”
奥诺里娜:“怪事,勒皮克先生在他家的女仆面前会这样拘束!他只要一开口,我马上就会给他换个杯子。”
勒皮克太太:“可能,奥诺里娜,最糟的就是你再这么刁钻也无法让一心沉默到底的勒皮克先生开口这种事连我自己也不愿再试了。不过问题还不在这里。总的一句话:你的眼睛愈来愈不管用了。要是你只干粗活,比如说洗洗什么,那还不太要紧,那些细巧事,你根本就干不了。尽管要增加家里开支我还是想再雇个人来帮助你……”
奥诺里娜:“我决不同意跟另外一个女人搅在一道,勒皮克太太。”
勒皮克太太:“我刚才就是说的这个。怎么办?老实说,你叫我怎么办好?”
奥诺里娜:“就这样我一直干到死。”
勒皮克太太:“你死!你想到死了吗,奥诺里娜?你也许比我们一家子都活得长呢,我真这样希望,你以为我指望你死吗?”
奥诺里娜:“你大概不会为了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就歇我的工吧。我告诉你,除非你赶我出去,我自己是不会离开你们家的。要是给赶出去,我不就是死路一条吗?”
勒皮克太太:“谁说要赶你走的,奥诺里娜?看你这样脸红脖子粗的,我们不过是心平气和的彼此谈个心罢了,好,你这下子就生了气,你讲了这一大堆蠢话,比教堂还大。”
奥诺里娜:“天哪!这怪得了我吗?”
勒皮克太太:“也不能怪我吧?你眼睛不好,既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我希望能医治得好,总有那么一天能好。可是目前,我们两个人里面,哪个最为难呢?你甚至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眼睛有毛病,可是我们家的家务却陷入了困难。我现在一片好心对你说这番话,是因为预防发生意外事件,同时也因为我似乎还有这个权力讲话,对你温和的指出这个毛病。”
奥诺里娜:“随你高兴。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勒皮克太太。刚才我都以为要给你赶出门了,现在我才放了心。这以后,我一定仔细把盘子擦干净,我保证。”
勒皮克太太:“别的我还要求你什么呢?我这个人也不像外面传说的那样坏,奥诺里娜,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不要你的。”
奥诺里娜:“既然这样,勒皮克太太,你就不要再说了。我自信还有用,要是你现在赶我走,我就要大喊冤枉了。可是等到有一天,我发现我已经成了你们的负担,连在炉子上烧一壶开水都不行了,你们就不叫我走我也要走。”
勒皮克太太:“记着,奥诺里娜,无论如何,我们家总有你一碗肉汤吃。”
奥诺里娜:“不,勒皮克太太,肉汤不必,有点面包就够了。你看玛义特大娘一直光吃面包,她也没有死。”
勒皮克太太:“你可知道她至少已经有了一百岁吗?还有一件事你知道吗,奥诺里娜?乞丐都比我们幸福。”
奥诺里娜:“你既然这么说,我也跟你一样说,对啊,勒皮克太太。”
[胡萝卜须给勒皮克先生的信和勒皮克先生给胡萝卜须的回信](选辑)
********************************************
<胡萝卜须给勒皮克先生的信>——寄自圣玛克学舍
********************************************
我亲爱的爸爸,
暑假里老是钓鱼,这可把我的身体搞坏了。我两条腿上都生了好多疮。现在,我躺在床上,护士在给我贴膏药。前些时疮还没有出头的时候,真痛。脓头出来之后我就不觉得了。可是这些疮正像小鸡似的蔓延开来。一个才好,又有两三个冒了出来。我希望不久会好起来。
*******************
<勒皮克先生的回信>
*******************
亲爱的胡萝卜须,
现在你既然去准备参加初领圣体,去听教理问答,你应当知道人类遭受钉子的痛苦并非从你开始。从前耶酥基督的手脚都被钉上过钉子。那些钉子都是真的,但他却毫无怨言。
鼓起勇气来吧!
你的父亲
***************************
<胡萝卜须给勒皮克先生的信>
***************************
我亲爱的爸爸,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刚出了一个新牙齿。虽然我还没有到年龄,我想,这是一个早熟的智慧齿,我希望还会有新的长出来。我保证行为端正,奋发用功,使你得到安慰。
你的爱子
*******************
<勒皮克先生的回信>
*******************
亲爱的胡萝卜须,
正当你出牙齿的时候,我有颗牙齿活动了。昨天早上它才掉。因此你虽然多了一颗牙,你父亲却少了一颗。所以一切都没有变化,家里人的牙齿总数,仍然无增无减。
**************************
<胡萝卜须给勒皮克先生的信>
**************************
我亲爱的爸爸,
真想不到竟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昨天是我们拉丁文老师雅克先生的生日,班上一致推举我代表全体同学,向他致贺词。我受宠若惊,用了好长时间准备了一篇讲话,其中还引用了几句拉丁文,老实说,我对此挺满意。我把它抄在一张重磅笺纸上。这一天,同学们都鼓励我,悄声说着:“上去,快上去!”——我趁雅克先生目光不注意我们的时候,朝讲台走去。想不到我刚刚展开笺纸,音节铿锵的念道:“尊敬的老师……”
雅克先生气冲冲的突然站起来,大声叱叫:“快给我滚回到自己座位上去!”
我只好一转身又溜回座位,同学们一个个把头都埋在书后面。这时雅克先生怒气还没有全消,命令我说:“你把这一段翻出来。”
亲爱的爸爸,你对此有何看法?
******************
<勒皮克先生的回信>
******************
亲爱的胡萝卜须,
将来有一天你当上议员,你会懂得这类事情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守。人家央请你的老师站上讲台,大概是要他讲话,而不是让他听你讲话。
**************************
<胡萝卜须给勒皮克先生的信>
**************************
我亲爱的爸爸,
我刚刚把你带来的野兔给我们的历史老师送去,勒格里先生看来非常高兴,他十分感谢你。我走进他家的时候带着一把湿漉漉的雨伞,他亲自从我手里接过去,放在门堂里。随后我们谈了话。他说要是我努把力,学年终了准能获得史地第一名。不过,你知道,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一直站着,他就是不请我坐下。除此以外,勒格里先生对我非常客气。
究竟是他忘记了,还是没有礼貌?
我不明白,但很想知道,亲爱的爸爸,我想听到你的意见。
******************
<勒皮克先生的回信>
******************
亲爱的胡萝卜须,
你什么都抗议。因为雅克先生叫你坐下,你抗议。勒格里先生让你站着,你又抗议。你这么小,就处处要求别人对你尊重,兴许太年轻了些吧。要是勒格里先生没有请你坐下,你该原谅他才是:这大概是因为你个头小,他误以为你坐着吧。
**************************
<胡萝卜须给勒皮克先生的信>
**************************
我亲爱的爸爸,
听说你要去巴黎,让我分享你游览首都的乐趣吧。——我也很想认识这地方,我的心将跟你在一起。因为学校里还有功课,我不能跟你同去旅行,但是我想趁此机会请求你,不知能不能替我买一两本书。我现有这些书早已读熟了,请你随便挑几册书。实质上书的价值都是相等的。可是我最喜欢的是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德·伏尔泰(*1)的《昂里阿德》和卢梭(*2)的《新爱洛绮丝》。要是你把这些书带来(巴黎的书非常便宜),我敢保证监学先生不会没收它们。
******************
<勒皮克先生的回信>
******************
亲爱的胡萝卜须,
你跟我讲的这些作家也是跟你我一样的人,他们所做的,你也能做到。你可以自己写几本书,自己去读。
**************************
<勒皮克先生给胡萝卜须的信>
**************************
亲爱的胡萝卜须,
今天早上我收到你的信,这真叫我诧异。我白白的看了几遍,好是不明白。你平常的文笔不是这样,而且这次信里你谈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物,我看,你不懂,我也不懂。
平常你在来信中总是跟我们讲一些琐碎事情,告诉我你在学校里的名次,你在各个老师身上发现的优缺点,你的新同学的名字,你的衣服如何如何,饮食睡眠好不好等等。
上面这些才是我所关心的事情。今天这封信却搞得我莫名其妙。请问你,现在正是冬天,你怎么讲起春天郊游的事呢?你究竟想谈什么?你是需要一条围脖儿马吗?信上连个日期都没有,简直不知道你这是写给我的呢,还是写给一条狗的。你的字体都好像变了,分行,大写的款式都令人不知所云。总之,你像在嘲弄什么人似的。我猜你是在嘲弄自己吧。我现在并不是想说你犯了过错,我不过是提醒你罢了。
****************
<胡萝卜须的回信>
****************
我亲爱的爸爸,
我现在功课很忙,为了跟你说明一下上一封信,我只想写一句话。你没有看出我那封信是用诗句写的吗?
*****************************************
译者注:
1: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
2: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
*****************************************
[银币]
<一>
勒皮克太太:“你没有丢东西吗,胡萝卜须?”
胡萝卜须:“没有,妈妈。”
勒皮克太太:“你还没看,怎么就说没丢呢?先把口袋翻翻。”
胡萝卜须:(他把所有口袋夹里翻过来,望着这些就象驴耳朵似的耷拉着的口袋)“啊!对了,妈妈!你还我吧。”
勒皮克太太:“还你什么呢?你丢了什么东西,是吗?我是随便问问你的,却让我猜对了!你究竟丢了什么?”
胡萝卜须:“我不知道。”
勒皮克太太:“当心!你想说谎啦。你真像一条粗心的欧鲌鱼,专门乱冒乱窜。你慢慢说。到底丢了什么东西?你的陀螺是不是?”
胡萝卜须:“真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对,妈妈,就是我的陀螺。”
勒皮克太太:“不,宝贝儿,不是你的陀螺。你的陀螺上星期已经被我没收啦。”
胡萝卜须:“那么,是我的小刀。”
勒皮克太太:“什么小刀?谁给了你一把小刀?”
胡萝卜须:“谁也没给。”
勒皮克太太:“我可怜的孩子,这话嘛我们真永远讲不清了。别人会说是我把你搞疯了哩。可是现在就我们两个。让我来心平气和的问问你。一个疼爱母亲的孩子应该什么话都告诉他母亲。我敢说你把你的那块钱丢了。这件事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我想我一定说对了。你不必否认。你的鼻子在翕动哩。”
胡萝卜须:“妈妈,这块钱是我的。是我的教父星期天给我的。我给丢了。真倒霉。这事真叫我懊恼极了,不过我会自己安慰自己。况且少一块钱多一块钱,我也不能把这事老记在心上。”
勒皮克太太:“瞧你这股瞎吹劲儿!我还正经八本儿的听你说呢。这么说你对你教父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竟满不在乎,是不是?他是那么疼你,要知道了,准会气坏了他!”
胡萝卜须:“妈妈,你就算这块钱已经让我信手花了。难道说我要把它放一辈子!”
勒皮克太太:“够了,讨厌鬼!你既不应当把它丢了,也不应当没得到家里允许就把它浪费掉。你现在钱已经没有了;你得想法把它补起来,找出来,去造一个,你自己去弄。滚吧,我不听你犟嘴子。”
胡萝卜须:“是,妈妈。”
勒皮克太太:“我不许你再说‘是,妈妈’,装模作样;要是我再听到你嘴里哼哼唱唱,牙齿缝里吹唿哨,学那些吊儿郎当赶马车的样儿,你当心,我不许你跟我来这一套。”
<二>
胡萝卜须在花园的小径上慢步走着。他尽叹气,他寻找一会儿又时时猛力用鼻子嗅嗅。当他觉得他母亲在注视他时,便站立不动,或是弯下腰,用指尖在酸模草和沙土中间搜索。在他想到勒皮克太太已经不在身边了,他就不再找下去,他只是做做样子,仰头向天继续走去。
这块银币究竟在哪里?是在高高的树上,在老鸹窝里吗?
有时有些人漫不经心,什么也不寻觅,可他们却找到了金钱。这事有人曾看见过。可是胡萝卜须哪怕他匍匐在地上,用膝头,用爪子,也找不出一根别针。
胡萝卜须对这种漫步,这样无名的希望已经感到腻味了,他干脆扔下不管,决定先回到屋里去看看他母亲的情况。兴许她已经平静下来,兴许她觉得银币既然找不到,干脆算了。
他没有见着勒皮克太太。他挺不好意思地,轻声喊着她:“妈妈,喂,妈妈!”
没人回答。她刚出去,屋里那张针线桌子的抽屉大开着。在那一堆毛线,针,白色、红色、黑色的线团中间,胡萝卜须一眼瞥见几个银币。
这些银币好像老在那里似的,仿佛在那里睡着了,很少被人惊醒过。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散散乱乱不知道有多少。
好像有三,四个,也许是七八个,很难计数。只有把抽屉整个翻遍,抖抖线团才行。可是,钱数怎么查得出呢?
胡萝卜须凭着那股子机灵劲儿,(只有在重大关头才会失去吧),一狠心,伸出胳膊去偷了一个银币,拔腿就跑。
他害怕被人家碰着,他毫不犹豫,满心懊悔,再也不想冒险回到那张桌子面前。
他直往外跑,急匆匆地一步不停,走遍了园中小径,去挑一块合适的地方,“丢”了这块钱,用脚把它深深地踩进土里,自己也趴下来,鼻子给青草搔得痒苏苏的,他随心所欲的乱爬,画出一些不规则的圆圈,就好像在一群孩子游戏当中,有人给蒙住眼睛围着什么藏起来的东西转悠,而旁边那个逗引瞎子的人正焦灼地拍着腿,大叫:
“当心!块碰着啦!快碰着啦!”
<三>
胡萝卜须:“妈妈,妈妈,我找着啦。”
勒皮克太太:“我也找着了。”
胡萝卜须:“什么?呐,这里有了。”
勒皮克太太:“我这里也有了。”
胡萝卜须:“好!给我看看。”
勒皮克太太:“你给我看看。”
胡萝卜须:(他把银币拿出来。勒皮克太太把她的一块也拿了出来。胡萝卜须把两个银币盘来盘去,比较着,准备他的话)“真奇怪,你在哪里找到的,妈妈?我嘛,我是在这条小路上,那棵梨树底下找到的。我起初在它上面走过二十遍,都没有看见。她闪着光,我先还以为是一张纸,或者是一朵白色堇花呢。我没有敢拿。这钱大概总是哪一天我在草地上打滚的时候从口袋里滑出去的。妈妈,你弯下身来看看它躲藏的地方吧。真厉害,她居然把我搞得这样心烦意乱。”
勒皮克太太:“你刚才的话我也相信。我呢,我是在你另外一件短大衣外套里找到的。我跟你说过多少回,换衣服时要把口袋都清一清啊,可你总是记不住。我想给你一个教训,做事要有条理。我让你去找,让你明白下回不能这样。可见‘努力找,总找到’这句老话可真对。你瞧,你现在不是有一个银币了,而是有了两个。好啦,你现在可浑身都是钱啦。固然,凡是好事总有好结果,不过,我得告诉你,金钱并不能使人幸福。”
胡萝卜须:“那么,妈妈,我可以去玩了吗?”
勒皮克太太:“当然可以。你去玩吧,你现在正是该玩的年龄。把你的两块钱拿走吧。”
胡萝卜须:“啊!妈妈,我要一个就够了,就连这一个我还要请你替我收着,等到我要用的时候再给我。我好心的妈妈。”
勒皮克太太:“不,好朋友也得明算帐,你自己把钱拿上。一个是你教父给你的,还有一个是你在梨树底下找到的,只要那个失主不来讨,两个都是你的。这钱是谁的呢?我实在想不出。你呢,你能想得出来吗?”
胡萝卜须:“我更想不出来了。先不管这些了,我明天再去想吧。一会儿见,妈妈,谢谢你。”
勒皮克太太:“等一下!这是不是管园人的?”
胡萝卜须:“你要我这就去问他吗?”
勒皮克太太:“站在这儿,小家伙,帮我想想。好好想。你父亲,他那么大年纪了,不会这样疏忽。你姐姐把她攒的钱都放在扑满里。你哥哥根本没钱可丢,手头哪怕有一个子儿也用得光光的。这样排下来,可能还是我丢的。”
胡萝卜须:“妈妈,我看不会;你从来办事细心。”
勒皮克太太:“有的时候大人也跟小孩子一样会弄错的。总之,以后再说吧。无论如何这事只跟我有关。我们现在不谈这件事吧。你别管啦,快玩去,我的大孩子,别走得太远,让我去看看我那针线活桌子的抽屉。”
(已经飞奔出去的胡萝卜须,这时又折回来,他目送着他的母亲渐渐走远。终于,突然,他走到母亲面前,拦住她,一声不响地将脸颊送过去。)
勒皮克太太:(抡起右手,好像要打下来似的)“我就晓得你在扯谎,但我还想不到你会这样厉害。现在,你扯了两个谎。这样下去,开始偷一只鸡蛋,接着偷一头牛,再往后就要谋杀他的母亲了。”
(第一个巴掌猛地落下。)
[个人的想法]
晚间,勒皮克先生,大哥费利克斯,姐姐埃内斯蒂娜和胡萝卜须一块儿坐在壁炉旁边闲谈。壁炉里熊熊地燃烧着连根的树桩子,四把椅子都翘着前腿,晃个不停。大家争论着,刚好勒皮克太太不在场,于是胡萝卜须便发挥起他个人的高见来了。
“据我看,”他说,“家族这个称呼是没有多大意思的。爸爸,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然而,我爱你,并不是因为你是我的父亲;我爱你,乃是因为你是我的朋友。老实说,你并没有任何功劳做我的父亲,但是我把你对我的友谊看做一种崇高的恩宠,这种恩宠你不一定非给我不可,而你竟慷慨的给了我。”
“啊!”勒皮克先生回答。
“我呢,那我呢?”大哥费利克斯,和姐姐埃内斯蒂娜抢着问。
“那也一样。”胡萝卜须说,“偶然使你们做了我的哥哥和姐姐,我为什么要感激你们呢?要是我们三个都不生在勒皮克家,那又能怪谁?这件事你们谁也无法阻挡。对于这种并非自愿的亲属关系,我根本毫无特别的欢欣。我所要感激你们的只是,你,哥哥,因为你保护我,你呢,姐姐,因为你给了我妥善的照顾。”
“这是我应当做的。”大哥费利克斯说。
“他打哪儿生出这样一些古怪念头?”埃内斯蒂娜姐姐说。
“我所说的话,”胡萝卜须说,“我是基本肯定的,但并不具体地说谁,就是妈妈在这儿,当她面我还是这么说。”
“你不会重说一遍的。”大哥费利克斯说。
“你觉得我的话有什么不好?”胡萝卜须回答。“请你不要歪曲我的思想吧!我不是个绝情的人,我心里爱你们比表面上流露出的还要强烈。不过这种爱心,不是平庸的,本能的,俗套的,而是有意识的,理智的,合乎逻辑的。对,合乎逻辑的,这正是我要寻找的词儿。”
“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这种脾气呢?老是爱用你自己都不懂的词儿。”勒皮克先生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准备去睡觉,“岁数这么小,还要拿来四下兜售。要是你祖父还在,听到我说句把句像你说的这种话,他一准马上就会给我一脚,再不就是一巴掌,表示我终究不过是他的孩子而已。”
“可是我们总得聊点什么,消磨时间。”胡萝卜须说,他已经有点不安了。
“你不讲话还要好些。”勒皮克先生说,手上拿着一根蜡烛。
于是他走开了。大哥费利克斯根在他后面。
“希望你睡个好觉,老朋友!”他对胡萝卜须说。
接着姐姐埃内斯蒂娜站起身,神色庄重地说:
“晚上好,亲爱的朋友!”她说。
只剩胡萝卜须一个人,茫然不知所措。
[胡萝卜须的照相册]
<一>
如果一个陌生人翻看勒皮克家的照相册,他免不得要吃惊,他看到姐姐埃内斯蒂娜和大哥费利克斯各式各样,穿着漂亮服装,或是日常衣着,或站或坐、或笑或颦,在富丽堂皇的背景前面拍摄的照片。
“胡萝卜须的呢?”
“我本来有他挺小时候拍的几张照片的,”勒皮克太太说,“因为他照得那么可爱,都让别人抢去了,我连一张也没留下。”
事实上是根本从来就没有人给胡萝卜须照过相。
<二>
大家一直都叫他“胡萝卜须”,也叫熟了,搞得家里人在喊他受洗的名字时都得怔一下。
“为什么你们叫他胡萝卜须呢?是因为他的黄头发吗?”
“他的灵魂更黄。”勒皮克太太说。
<三>
还有不少别的标记:
胡萝卜须的脸一点也不讨人喜欢。
胡萝卜须的鼻子像鼹鼠掘起的土堆。
胡萝卜须的耳朵里,不管人家怎么掏,经常总有着一些面包皮。
胡萝卜须可以把雪放在舌头上融化,吃下去。
胡萝卜须的脚步沉重,走相难看,像个驼子。
胡萝卜须的脖子上总是有一层蓝黝黝的老垢,好像戴了个项圈。
末了,胡萝卜须口味古怪,他还闻不出麝香来。
<四>
在家里他起得最早,总是跟女仆同时起身。冬天的早晨,天没亮他就下了床。他用手去看时间,手指头摸着钟面上的长短针。
当咖啡和巧克力煮好了的时候,他就在这儿站着,匆匆忙忙,捞着一块什么就吃。
<五>
当别人把他介绍给某人的时候,他反而转过身去了,从背后把手伸出来,一副厌烦的样子,蜷着双腿,搔弄墙壁。
如果人家问他:“你愿意亲亲我吗,胡萝卜须?”
他回答:“啊!用不着啦!”
<六>
勒皮克太太:“胡萝卜须,人家跟你说话的时候,得回答啊。”
胡萝卜须:“西,莫莫。”(*1)
勒皮克太太:“我好像早跟你说过,小孩子吃东西的时候不要讲话。”
<七>
他总是忍不住要把手插在衣袋里,一看见勒皮克太太来了,就赶紧把手抽出来,可惜已经晚了。总有一天,她发起狠来会把他的口袋跟手一道缝上。
<八>
“无论人家怎么样你,”教父和蔼可亲地对他说,“你说谎,都是不对,这是个坏毛病,况且说谎也没用,一切总要给人知道的。”
“对啊,”胡萝卜须回答,“可是我总可以挨过一阵子。”
<九>
那位懒惰的大哥费利克斯好不容易才在学校里毕了业。
他伸伸懒腰,舒舒坦坦地叹了口气。
“你对什么最感兴趣啊?”勒皮克先生问道,“你这个年纪,也该决定选个职业了。你想做什么呢?”
“什么!又来啦!”大哥费利克斯说。
<十>
大伙儿在一起闹着玩儿。
问题都集中在贝尔特姑娘身上。
“这是因为她有一双湛蓝的眼睛,”胡萝卜须说道。
“多美啊!好个风雅的诗人!”
“啊!”胡萝卜须回答,“我连她的眼睛都没有看。我说这话就象我说别的事情一样。这不过是老套子,一种修辞法罢了。”
<十一>
在玩打雪仗的时候,胡萝卜须独当一面,因为他在雪团里包着石头,大伙儿都害怕他,威名远扬。
他瞄准别人的脑袋:这比较快当。
地面结了冰,别人都在溜冰,他就在溜冰场旁边的草地上,自己另外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冰道。
在做“跳马”游戏时,他喜欢弓着身蹲着,让别人从他身上跳过去。
玩“抓俘虏”时,他总是不顾自身自由,任人家随意摆布。
玩“捉迷藏”时,他可躲得真好,人家都把他忘了。
<十二>
孩子们在比个头儿。
一眼望过去,大哥费利克斯比别人都高出一头,他不参加比赛。姐姐埃内斯蒂娜尽管是个女孩子,却跟胡萝卜须站在一道,差不多高。当姐姐踮起脚尖尽力拔高身量时,不愿意使别人不快的胡萝卜须,故意悄悄地蜷起身子,好使他俩的差距略略再大些。
<十三>
胡萝卜须给女仆阿珈特这样一个忠告:
“你要是想让勒皮克太太喜欢,你只要在她面前说我的坏话就成。”
可是事情总有一个限度。
除了自个儿,勒皮克太太不许别人碰胡萝卜须一下。
有一天,邻居的一个女人正在威胁胡萝卜须,勒皮克太太火冒三丈,马上跑过去,搭救她的儿子。她儿子满脸浮现出一片感激之情。
“现在,我们两个人来算算帐!”她对他说。
<十四>
“爱抚!这话是什么意思?”胡萝卜须问那个被妈妈溺爱的小比埃尔。
大概弄懂了之后,他叫起来:“我啊,我希望的就是用手指在盆子里拿炸土豆片吃,还有,就是吮吸连核的那一半桃子。”
他想了一下:
“要是勒皮克太太爱抚地咬我几口,她准是从鼻子开始。”
<十五>
有时姐姐埃内斯蒂娜和大哥费利克斯玩厌了,便自愿把他们的玩具借给胡萝卜须玩。于是他分享了他们的一小份幸福,适度地构成他自己的一份。
因为害怕他们向他讨还玩具,他从来不敢表现出过分高兴的样子。
<十六>
胡萝卜须:“那,你不觉得我的两只耳朵太长吗?”
玛蒂尔德:“我觉得你的耳朵挺古怪。可以借给我使使吗?我想把一些砂子装在里面做肉糜。”
胡萝卜须:“要是妈妈把我的耳朵点起火来,肉糜不就在里面煮烂了吗?”
<十七>
“你停住!让我再听一遍吧!啊,我跟你父亲相比,你更喜欢你父亲吧?”勒皮克太太不管到哪里,都说这句话。
“我呆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我对你发誓,你们两个我都不喜欢。”胡萝卜须心想。
<十八>
勒皮克太太:“你在做什么,胡萝卜须?”
胡萝卜须:“我不知道,妈妈。”
勒皮克太太:“这就是说你又在做傻事,你总是存心那样做。”
胡萝卜须:“我就差这一点儿。”
<十九>
胡萝卜须以为他的母亲在对他微笑,于是挺高兴的,也跟着微笑。
可是勒皮克太太,只不过是闲着没事,自个儿觉得好笑,她突然脸一板,那黑木头似的头上活像嵌着两颗黑茶藨子。
胡萝卜须,吓得手足无措,不知道往哪里逃好。
<二十>
“胡萝卜须,你不能文质彬彬的、不出声地笑吗?”勒皮克太太说。
“一个人哭的时候,应当知道为什么要哭,”她又说。
她还说:“你究竟要我怎么办呢?三巴掌都打不出他一滴眼泪来。”
<二十一>
她还说:
“要是空中有一个斑点,路上有一摊狗屎,这都算是给他的。”
“他的脑袋瓜子里总是有个什么好主意,可就是有头无尾。”
“他真骄傲,简直会为了引人注目而杀人。”
<二十二>
胡萝卜须确实想在一个盛满着清水的桶里自杀,他勇敢地把鼻子和嘴都浸在水里,可就在这当口,有个教士走过,把水桶带翻了泼了一脚的水,还救了胡萝卜须的命。
<二十三>
有时勒皮克太太对胡萝卜须说:
“你跟我一样,并不狡猾,与其说是坏,不如说是笨,脑袋瓜太死,想不出什么花样来。”
有的时候她又会承认,如果胡萝卜须不被小猪崽子吃掉的话,他将来准有出息。
<二十四>
“要是有一天,”胡萝卜须心里想,“就象给大哥费利克斯的那样,人家给我一只木马作礼物的话,我跳上马背就飞跑。”
<二十五>
在外面,为了表示自己什么都不在乎,胡萝卜须老爱吹吹口哨。可是一看到勒皮克太太跟在他后面,他就嘎然而止。这真难受,就好像他把一个小小的便宜哨子断在嘴里了。
然而,该承认一听到他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她便扔下他随便他去。
<二十六>
他成了父亲和母亲的联接线了。勒皮克先生说:“胡萝卜须,这件衬衫上少了一粒钮扣。”
胡萝卜须把衬衫递给勒皮克太太,她说:“难道我还要你来命令吗,傻瓜?”
不过,她还是拿出针线篮子,把钮扣缝上了。
<二十七>
“要不是你父亲在家的话,”勒皮克太太叫嚷着说,“你早就对我下毒手了,你早就把刀子捅到我心里,杀翻在干草上了。”
<二十八>
“把你的鼻子擤擤,”勒皮克太太时时刻刻老是这样说。
胡萝卜须不住地用衣裳摺边擤鼻涕。要是团皱了,他又把它抹平。
确实,当他伤风了,勒皮克太太给他涂上蜡烛,弄得非常脏,竟叫姐姐埃内斯蒂娜和大哥费利克斯都嫉妒起来。可是她特意给他补上一句:
“这与其说是毛病,还不如说有好处呢。这可以让脑子清醒清醒。”
<二十九>
因为勒皮克先生从今天早上起,便老在作弄他,胡萝卜须不知不觉冒出这么一句凶话:
“让我安静点,傻瓜!”
话一出口,他立刻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凝结了,眼睛里有两股热流涌了出来。
他嘟哝着,只要勒皮克先生一个手势,他简直要钻到地里去。
但是勒皮克先生朝他凝望了好久,没有做什么手势。
<三十>
姐姐埃内斯蒂娜快结婚了,勒皮克太太允许她在胡萝卜须的监视下跟未婚夫去散步。
“在前面走吧,”她说,“你跳跳蹦蹦地玩好了!”
胡萝卜须在他俩前面走。他拼命地跳啊蹦啊,如果他偶尔放慢脚步时,他便听见一阵啧啧接吻的声音。
他咳嗽了一声。
这事真让他激动,在走到村里的十字架前面时,他突然把帽子往地下一扔,用脚踩了踩,叫道:
“难道说就永远没有一个人爱我吗!”
刚好,就在这时候,勒皮克太太从墙后面伸出头来,嘴角浮现出一种可怕的微笑。
于是,胡萝卜须慌慌张张,赶紧添上一句:
“除了妈妈。”
洗澡
◎列那尔[法国]
快敲四点钟了,胡萝卜须很兴奋,叫醒了睡在花园里筷子树底下的勒皮克先生和费利克斯大哥。
“我们该动身了吧?”他说。
大哥费利克斯:“好,穿短裤吗?”
勒皮克先生:“现在天气大概还太热。”
大哥费利克斯:“我啊,我倒更喜欢有太阳的时候去。”
胡萝卜须:“爸爸,河边一定比这儿更叫你喜欢。你可以睡在河边的草地上。”
勒皮克先生:“你们前面走,慢慢的,走急了会受热。”胡萝卜须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步伐放慢,他感到脚上象有蚂蚁爬。他肩上背着他自己的那条挺老气、没有花色的和大哥费利克斯的红蓝两色相间的短裤。他容光焕发,不停地唠叨,他悄声儿唱歌,从路旁那些低垂的树枝上跳过去,沐浴在和风里。他跟大哥费利克斯说:“你以为这好玩吗,嗯?我们马上就在水里抖动两条腿!”
“小淘气!”大哥费利克斯回答,那样子显得轻蔑,胸有成竹。
这样,胡萝卜须立即平静下来。
他头一个欢快地跨过一堵石头砌的矮墙,面前就突然出现一条小河,河水在汩汩地流淌。现在不是说笑的时候了。
粼粼的波光映照在愉悦的水面上。
河水荡漾,象无数牙齿咯咯作响,发出一种淡淡的气味。
问题是该跳下河去,在水里倘样戏波,可是勒皮克先生还老是在凝神看表上规定的时间。胡萝卜须打了个寒颤。他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失去了早已鼓起的勇气。他望着水,这曾经远远地吸引着他的河水,一出现在面前,反而使他为难起来。
胡萝卜须躲到一边,开始脱衣服了。他倒不完全是因为怕他那一身瘦骨磷峋的身体和那双脚被人看见,而是因为这样他好一个人毫不害羞地颤抖。
他一件一件地把衣服脱掉,细心地在草地上叠好。他结紧鞋带,装着老半天解不开来。
他着上短裤,脱了短衫,因为浑身是汗,皮带粘得紧紧地包在身上就象苹果糖外面包扎着一层糖纸似的。他又等了一会儿。
大哥费利克斯早已下了河,占住一块河面胡乱扣腾。他用劲拍打,用脚踝碰击,河上泛起多少泡沫。他从河中间把咆哮的浪花驱向河边。
“你不想下去吗,胡萝卜须?”勒皮克先生问道。
“我晾干身子再下去。”胡萝卜须说。
随后他决定了,坐在地上,用那只被过紧的鞋勒坏了的脚趾先探探水。
同时,他摩掌着肚子,好象吃的东西还没有全消化。接着他沿着草根任凭身子滑下去。
草根搔着他的小腿肚,大腿和屁股。当河水浸到他肚子的时候,他又浮上来,溜了。他仿佛觉得有一根湿流液的绳索缠在他身上,象绕陀螺一样。
可是他倚傍的那块泥土松散开了,直往下坍,胡萝卜须跌到河里,水漫过了顶,他摸索着,把身子站定,水呛得他咳嗽起来。有点窒息,眼睛也看不清东西,弄得晕头转向。
“你这个‘猛子’扎得不坏,孩子。”勒皮克先生说。
“嗯”胡萝卜须说,“虽然我不太喜欢这玩艺儿。水灌到耳朵里了,我会头痛的。”
他找了一块可以学学游泳的地方,这就是说,在这里他可以活动手臂,运用膝盖在沙子上匍匐前进。
“你太急躁了。”勒皮克先生对他说,“拳头不要攥紧。不要象拔自己的头发那样攥紧拳头。两腿也不能搁着不用,要自由摆动。”
“游泳要是不用双腿,那可真难。”
可是大哥费利克斯老是来打扰他,不让他专心学习游泳。
“胡萝卜须,来这儿。这儿水比较深。我的脚碰不到底,我沉下去,你瞧。哪,你现在还看到我。注意:你看不到我了。现在,你站到柳树那边去。不要动。我可以打赌,只要划十下就能游到你那儿。“让我来数。”胡萝卜须哆嗦着,肩膊露出水面,一动不动真象个界标似的。
他又蹲下水去准备游泳。可是大哥费利克斯爬到他背上,一头窜进水里,说道:“现在轮到你了。你要愿意,爬到我背上。”
“让我安安静静做我的游泳练习吧。”胡萝卜须说。
“好啦。”勒皮克先生叫道,“上来吧,每人喝一点露姆酒。”
“已经要上来了吗?”胡萝卜须说。
现在他真的不愿意上来。他这场游泳还没有游好呢。这条他就要离开的河已经不叫他害怕了。刚才他还重得象一块铅似的,现在却轻得象一根羽毛了。他带着狂热在水里拍打,一点也不觉得危险,就象是拼命去救个什么人似的。为了尝尝溺水者的痛苦,他甚至自动沉人水中。
“快点上来。”勒皮克先生大声喊叫,“要不,你大哥费利克斯把露姆酒全喝光啦。”
虽然胡萝卜须不喜欢喝露姆酒,他还是说:“我的那一份谁也不给。”于是他象一个老兵似的把酒渴下去。
勒皮克先生:“你身上没洗干净,两只脚赚上还沾着污垢呢。”
胡萝卜须:“是泥土,爸爸。”
勒皮克先生:“不,是污垢。”
胡萝卜须:“我再下河去洗。好吗,爸爸?”
勒皮克先生:“你明天再洗好了,我们还要来的。”
胡萝卜须:“碰运气!天气好我们再来!”
他用大哥费利克斯弄潮了的那块毛巾的干角揩身子,只感到头脑发胀,喉咙干涩,他的哥哥和勒皮克先生拚命拿他又肥又粗的脚趾开玩笑,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